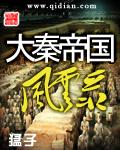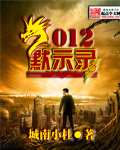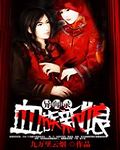五胡烽火录-第9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应该说阿拉法特简直是现代的阳骛。
1600年后,阿拉法特不过是弄了点阳骛的牙慧,就跟以色列玩这套“讲和”把戏,把以色列弄的打又不敢打,翻脸又没“道义”,最后狼狈不堪。
“大将,需要一员大将”,慕容恪自言自语:“宜弟的才能虽然不堪,然,两万精骑的战斗力我却知道,汉国能一举吃掉我两万精骑,实力也不简单。我们必须派一员大将主持袭扰,派谁去?”
“中领军慕舆根,鹰视狼顾,恰好为帅”,封奕不愿风头尽被阳鹜抢去,他乘机建言。
慕舆根也属慕容族,其人号称为“慕容氏之豺狼”,喜好杀俘虐俘,性格极其凶残,封奕指点慕容恪放出这条豺狼,暗示慕容族应该对汉国实行焦土政策。
“好”,慕容恪击节赞赏。
慕舆根像一把锋锐的匕首,他的声名来自他的残暴,这把匕首太锋利了,连慕容族在使用他的时候,也唯恐伤着了自己。慕容大军南下,所有的将军都有活了,连慕容宜这个废物都派出去了,唯独这位中领军慕舆根闲着。
慕舆根的悠闲不是因为无能,而是因为燕国还想长久统治所占领的幽冀之地,因而担心放这条疯狗出去,万一杀戮过狠伤了民心,燕国今后就不好管理了。
次日,汉国使节陈浩冒雪踏上回国的路,他将沿鲍丘河一路南下,穿过千里大沼泽(今唐山、玉田与武清之间的三角洲),抵达鲍丘河入海口(今天津),汉国的海船正在那里等他。
陈浩从蓟县南门出城时,燕国中领军慕舆根率一支骑兵出了蓟县东门,冒雪向辽西进发。后人谈到这时常常慨叹:改变世界的两个人,竟隔着这么近擦肩而过,若是这两人当时相逢,历史会是什么结局?
可惜,历史无法假设!
相比东门送别慕舆根的场面,蓟县南门显得冷冷清清,像慕容恪、慕容垂、阳鹜这样的燕国重臣都去了东门,此刻,南门只剩下了封奕一个人。
燕国不认为这是礼节粗疏,因为封奕是国相,国相亲送汉使,对于小国匠汉来说,已经很给面子了。
“没有使节随行”,陈浩望着心不在焉的封奕,微感失望。
虽然明知道燕国的许和很勉强,他也没指望燕国能派使节祝贺国主大婚,但事到临头,最后的侥幸心理被打碎,陈浩还是心里不舒服。
“告辞!”陈浩最终还是拱手作别。
“且慢”,封奕一直没解决他的疑问,心里有疙瘩,老觉得堵得慌。
想到陈浩回去发现燕军的袭扰后,汉国会彻底与大燕成寇仇,双方消息阻绝,他的疑问将再也得不到答案,封奕不觉拽住陈浩的衣袖,一横心,决定撕破老脸问个究竟。
“近芝(陈浩的字)兄,常言道:‘秦失之于苛,汉失之于宽’。秦法严苛而民怨,汉法宽松则豪族起,秦汉因此而国灭。
近芝兄也说‘汉国刑法严苛繁琐,比之暴秦有过之而无不及’,‘连走路,倒垃圾这样的小事都规定得很细’,却又说‘三山之美,正在于那繁琐的律法’,还提到‘规则社会’这个词。
奕自认为对治国之术略有心得,想当初,燕国不过是赵国连续攻击下,暂存性命的一个辽东部落,奕与众人筚路蓝缕,打下眼前这个大好局面,眼见得天下在手,奕正想指点江山一番。可治天下,到底用宽刑好还是用苛刑,望近芝为我解惑!”
陈浩悚然而惊。
燕国现在已经在考虑“治天下”的事了?
封奕一代国相,竟能放下架子,问一个小国使节,难怪燕国能够崛起于辽东!
汉国也能做到这点吗?
陈浩心里打了个转,还是给了肯定的答案。
能!蛮夷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胡人能放下架子学汉学,然后奴役汉民,我们也该谦逊地低下头,学习蛮夷的长处。
我们本当如此,才能免于种族灭绝!
“刑律无所谓宽苛——不,刑律压根就没有‘宽苛’的区别”,陈浩点点头,老实地回答:“刑律之道,就在于持平。持平,则无所谓宽苛。”
这话符合法家学说的一贯说法,但就是太笼统,等于什么都没说。
封奕不甘心,继续追问:“看来,近芝在三山所见,已有心得,可否说的再详尽点,为我解惑?”
陈浩仰脸看了看天空,又望了望四周,似乎在考虑如何措辞,实际上是在衡量该不该说三山的命运。
封奕也不催促,但他没有放松手中的衣角,只静静的等待。
阴历的立春还没有到,但实际上,当时已是阳历的元月末。不远处,鲍丘河已经化冻,河面上不时传出冰块撞击的巨大轰鸣声。
陈浩眼珠一转,一指鲍丘河方向,说:“我汉国也有一条河流,名叫沙河。当初,汉王创立基业时,命令汉人居于左岸,宇文部居于右岸……”
封奕放开了陈浩的衣角,抄着手饶有兴趣的听对方说话。
听说,铁弗高是墨家弟子,看来三山真是尚古啊。这种用寓言方式讲故事说道理的谈话技巧,许久不闻了。嗯,我倒是要好好听听。
“……汉部以耕作为业,宇文部以牧马为生”,陈浩悠然的继续说:“可是汉部耕作缺少畜力,宇文部放牧缺少粮食,而后,两部庶民相约互助,宇文部出牲畜,汉民用粮食偿付畜力。
两部庶民习俗各不相同,对于畜力价值各有认定,随着两部百姓的交流,民间争执日盛。此后,我王召集两部庶民制定约法,平息争端。
两部庶民一河相隔,春雪消融时正是需要畜力的时候,然而河中巨冰漂流。每当此时,两河百姓隔河相望音信不同。
争执平息之后,我王便在沙河上搭建一桥。河中心是座巨石搭建的汉王塑像,汉王双肩担起桥面,形似一条扁担横贯河面。河面两头各有一座矮堡,形似水桶。一堡名‘天’,一堡名‘平’。后来,汉国商贾模仿这座桥的形状,制作一衡器,名为‘天平’。
在下初到汉国时,甚苦其刑罚苛责,也曾萌生去意,然忽一日,我在桥上看到汉王塑像基座上刻的两行大字,便豁然开朗。从此,不以律令繁苛为苦,封公可想知道这两行字是什么?”
不等封奕回答,陈浩朗声长吟:“规则至上,王在法下。”
说罢,陈浩一拱手,扬长而去。
封奕震惊的无以复加,竟没有察觉陈浩何时离开,他梦呓般的反复念叨这两句话:“规则至上,王在法下……规则至上,王在法下……”
天平,对了,“规则至上”就是公平。所以那个桥才叫天平桥。“王在法下”,才能保证规则不被破坏,生活在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甚至连王本人也须接受的规则下,才有诸族平等,诸生平等。
可是,这样就算了吗?王在法下,能行吗?“天、地、君、亲、师”,君是仅次于天地的“神”,是“君无戏言”,是“出口成宪”的“天之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犯了错,也要接受律法的惩处,那“天人感应”到哪里去了?“天人合一”怎么办?
封奕一声长叹,他到此时终于明白了三山人心齐的原因,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陈浩毫不避讳的揭开这个秘密原因。
他就是知道了,也无法实施。因为燕国的政权已经成型,鲜卑部落的酋长们依靠驱使他人征战杀伐,任意践踏人世间的一切公理,虏获了巨大的财富,他们以强势姿态凌驾于各族之上,甚至凌驾于本族奴丁,他们不会与别人讲公平。他们不会愿意接受规则的束缚。
如果硬要设立一个规则让他们遵守,那他们设立的一定是吃人的规则,如此一来,这个政权将崩溃的更快。
封奕的思绪从来没有如此混乱,他头痛欲裂:“子曰:‘天不变,道亦不变’,如今,道已经变了,天变了吗?”
仿佛老天听到了封奕心中的呼唤,一骑快马飞驰而来,像一只乌鸦一样,带给封奕天变的消息:“国相大人,燕王陛下请你速速回宫,龙城传来消息,侨郡民变。”
第二卷 艰辛时代 第1108章
所谓侨郡,指的就是汉人聚居的乡镇。
西晋末,八王之乱时,匈奴羯胡接连进入中原,汉族流民四处逃亡,寻找能够安下一张床的平静之地。慕容隽的爷爷甚有政治远见,他大力招揽汉族流民,在辽水流域设立了数个侨郡。
比如,以冀州流民组成的屯民点被称为冀阳郡,豫州流民组成的屯民点为州郡,等等。从此,“侨”这个词有了旅居他乡的含义。后世所谓的“华侨”就是从慕容鲜卑的侨郡演变而出的词。
当时,五胡以汉民为下等民族,其中羯胡甚至把汉人当作一种“两脚羊”,饥饿时可以直接宰杀,煮而食之。在这种氛围下,压在汉民头上的赋税较重,很多时候,他们本身就是胡人的一种食物。
慕容隽的爷爷招徕汉族流民后,恢复了曹操所实行的屯田政策,汉侨们若是租用鲜卑族的牲畜耕田,收获按六四分成,官六民四。若部族用牲畜,则收获对半分,官民各占五成。
古代百姓的负担分为税与赋,税是当地官府征收,主要用于维持官府运作。赋是供养皇帝花天酒地的费用。汉侨缴纳的这五成以上的收获属于“税”。此外,他们还要承担沉重的“赋”,还要加上各种名目繁多的“役”。
即使按五五分成,汉侨们的负担也是极其沉重的。他们一年辛劳到头,基本上除了勉强维持生命的食物别无所得。然而,慕容鲜卑用这样的赋税水平对待汉民,却是胡人中对汉人最为宽容的——起码他们不吃汉人。
慕容鲜卑正是因为吸纳大量的汉侨,才慢慢的从一个实力不彰的小部族变成辽东最强大的政权。
战争打得就是经济,打得就是粮草。慕容鲜卑拥有着上百万任劳任怨的汉侨,它的常备军数量多的令人发指。汉侨的辛苦劳作,可以让慕容鲜卑聚集起数十万大军常年在外作战。仅仅依靠拖延战术就可以让实力不济的小部族经济崩溃,无力再战。
可以说,汉侨是慕容鲜卑强大的基础,汉侨稍有异动,强大的慕容鲜卑就会变得像纸糊的老虎一般脆弱。
“天,真的要变了”,封奕心中隐隐产生了一丝恐惧。
汉侨的招抚正是在封氏家族、阳氏家族、皇甫家族等数代汉臣努力下达成的。以前,三山汉国从没停止向燕国的汉侨使媚眼,然而,燕国的强大让侨民有一种安全感,他们担心,汉国虽然赋税较轻,然而国力的弱小却不能给与他们安全。
与其将来被屠杀,不如暂时忍受压榨——这是汉侨们的普遍心理。正是基于这个想法,高翼虽然竭力的招揽汉侨,但他只能找到一些零散的逃奴,形不成规模。
然而,当汉军冬季大胜燕军的消息传到龙城之后,多米诺骨牌倒下了第一张牌。
战争结束一个多月后,艰难的穿越了积翠山的溃军幸存者来到了辽河平原,他们诉说着汉军的残暴,于是,多米诺骨牌的倒下了倒下了第二张牌。
中国历史中,对这段杀戮时代的胡人习俗没记载,当然,俺们的精英们历来对生活习俗不感兴趣,连本民族的生活习性也懒得记载。俺们写的所谓24史,只是历代帝王“起居录”与“帝王家谱”。尤其是五胡时代的历史,更是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甚至是禁忌的历史。汉人当政时,要顾及民族感受,不准说;胡人当政,要坚决篡改与抹杀。
相反,同一时期,与当时胡人同一生活方式的匈奴人,被我大汉驱逐之后,正在蹂躏欧洲,欧洲人对其生活习性记述得很清楚。
从史书上记载的片言只语,再对比欧洲人对匈奴部族的生活习性记述,可以看出当时五胡部落的许多风俗,其中,汉侨大规模逃亡的主要诱因是鲜卑贵族的春季“索贡巡游”。
燕国连年战争,虽然连续取得辉煌的胜利,但是其下辖汉侨最后的潜力已被压榨的没剩一点渣子。当积雪开始消融的时候,在帐篷里窝了一个冬天的鲜卑贵族开始了年度春季巡游(我们的史书把它称作“春狩”,或者“春巡”)。
表面上看,这种春狩是视察领民冬季的损失情况,并清点自己的“财产”,做好春耕准备。但实际上,这是一次“索贡巡游”。
鲜卑贵族整整一个冬天都在吃自己的牲畜,到了春天,按照鲜卑习俗,他们需要从汉侨那里得到一些补偿。
积雪初溶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基本上,所有的汉侨已吃光了去年秋季的积粮,连地主家余粮也不多。鲜卑贵族的索贡巡游,按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三张。
此后,联动效应轰然爆发,乘着鲜卑族尚未聚集起足够的兵力堵截,辽河流域的各大侨郡爆发出大规模逃亡热潮。得到消息的侨民乘着鲜卑族尚未走出帐篷,丢弃家里所有的家资,携妻带子,踏着初春的残雪向汉国奔跑。
跑!快跑!你老兄怎么还背着破锅,扔了吧。俺家邻居去年跑到了三山,听他说,你只要人到了,官府就给你发东西。农具、种子、土地……连老婆都发。嘿嘿,听说倭国的小娘们皮肤又白又细,比你家的大黑驴还听话。
跑,人到那里就成……啥?要不要钱?不要钱。土地、农具、房子、种子,还有那又白又嫩的倭国小娘子都不要钱,白给。粮食打下来,连税负都不用交。汉国人吃粮怎么办?拿钱买。那里的大王可和善了,拿钱跟自己的庶民买粮吃。啧啧,天底下哪找这样和善的大王?跟手下要粮不用刀,用钱砸你。
什么?你识字?那大人今后可要多照应我了,听俺的邻居说,他们那疙瘩把识字的人都叫“城里人”,只要你识字,就可以搬到三山城里住。
俺听说,三山城可富了,全是白色的大石屋,风吹不走,雨淋不上,天天吃肉,穿得那叫好啊。火浣布,知道吗?三国时那可是奇珍啊,皇帝都捞不到穿。据说是一种花织成的……叫棉花。
城里人那个富啊,他们人人都穿火浣布,穿一套扔一套。你老兄可是要享福了。
在这样似是而非的传言耸动下,侨郡人心惶惶,机灵的侨民乘夜整郡整郡的逃亡。没走的侨民们探头探脑,一脸的诡秘神情,路上两熟人遇到一起,都不用语言交流,全用眼神。
一个眼神飘过去——你还没走啊?
一个眼神飞过来——没瞅见机会。
再一个眼神递过去——什么时间跑路?
猥琐的憨笑浮出来——得偷一匹马……奸笑ing。
“杀”,燕王宫里,慕容评暴跳如雷:“派快马通知慕舆根,让他杀光这帮贱奴。我就不信收拾不了这群人。这帮汉奴才过几天好日子,就忘了这好日子是谁给的?”
听了这话,殿上的汉臣面色尴尬,慕容贵族则脸色铁青。
没有了为慕容贵族无偿劳动的汉侨,这些鲜卑贵族怎样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继续操劳?
这是个问题,严重到动摇国本的大问题。汉奴咋就这样不愿意受压迫呢?太没有道德了,一点不讲忠恕!
“慕舆根的刀不需要磨”,燕王慕容隽阴沉着脸说:“汉侨的事情,由他放手施为。我们现在要商讨的是怎么阻止汉侨外逃。”
没法阻止,三山的高翼竖起大汉的旗帜,招引同族同种的同胞。这本就让汉侨具有亲切感,再加上他不征农税,承认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这让燕国拿什么来跟铁弗高争夺人心?
燕国马上要展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