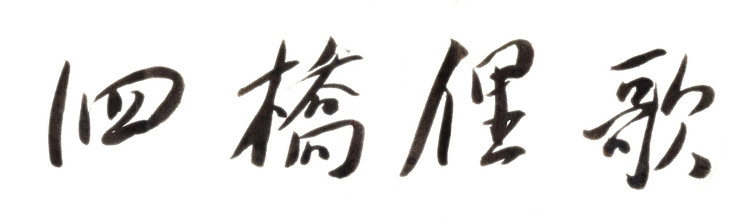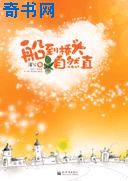李家桥-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只是这担忧,因着素陌平生,不过是一段同路而行的交情,若是明白讲出来,难免交浅言深。
柴房之中,一时间又安静下来。
三人却不知道,张斗魁此时正对着顾岳背包里的东西恼火不已。
白日里各路劫匪抢来的财物,交上来时都要一一清点记数,此时都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顾岳背包里搜出来的十七块大洋、七瓶白药自然也在其中,至于衣服杂物之类的,本来是要和其他抢来的杂物一道随便堆在角落里、临走时随手分给村民结个善缘的,因着张斗魁对顾岳的来历生出疑心,特意将背包里的东西仔细清点了一番。
顾岳的背包里,除了几件寻常换洗衣服之外,另有两套洋学堂的学生衣裤,一条薄毛毡,两条绑腿布带,一支自来水笔,一条皮带,一包防水油纸密密裹好的书,以及两封信,收信人是云南昆明翠湖街顾品韩,寄信人是湖南阳县李家桥顾韶韩。
张斗魁读过几年书,一看这寄信人的姓名,便冲口而出:“操他奶奶――”
其他两名头领,也稍识得几个字,看了信封,面面相觑,大概明白张斗魁心里的憋闷与恼火了。
阳县共有三个地方叫做李家桥,但是能够养得出顾岳这样子弟的顾家,却只有一个李家桥之中有,就是大明山下五十里处清江河畔柏树湾的那个李家桥。
李家桥得名于清江河上那座由李氏一族捐建的石桥。其实当地大族,共有李、顾、何三姓,世世通婚,家家习武,自前清以来,世道越来越不安宁,李顾何三姓为保乡里安宁,陆续买了洋枪和抬炮,修建石墙,又送子弟出去读书投军,尤其是顾家子弟投军的多,虽然还没听说出了什么督军之类的大人物,但也足以让阳县当地人敬畏避忌了。大明山上的土匪,都知道李家桥不好惹,李家桥也没想过要替天行道将五十里外的大明山清理干净,故而一直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遇上,也是互相避开了事。
这一回,顾家子弟打伤了大明山的劫匪,大明山的劫匪又将顾家子弟绑了肉票,这团乱帐,还不知怎么才能扯得清楚。素来都说,一山不容二虎,现在两个山头的老虎不当心遇上了,还互相抓了一爪子,谁先退让一步,都会被围观的群兽认定是胆怯畏缩,虎落平阳还被犬欺,何况是倒了威?
一名头领懊恼地道:“那小子怎地不说清楚自己的来历?”弄得现在骑虎难下了。
另一名头领弹弹信封:“看这收信地址,这小子多半是在昆明长大的,根本不晓得老家的这些事。”
一边说着,一边拆开了那包书。
油印的书页,薄而软,纸面发黄,并不起眼,然而十来本书,皆是《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军制学》、《卫生学》、《步兵操典》等武学堂的教材,封面的书名之下,都印着“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字样,扉页上又都写着“第12期丙班顾岳”的字样。
堂屋里一片寂静。
张斗魁和另外两名头领,都算是有见识的,不然也坐不上这个位置。
因为有见识,自然也明白顾岳的份量。
前清以来,各地立了不少武学堂,但是最有名望最有影响的,无过于保定军校和云南陆军讲武
堂,这两个武学堂,听说教官大多是留洋回来的,那些学生也有出洋的,但更多地是进了各地的新军,天南地北,无处不有,说不好哪天碰上的带兵长官就是这两所学堂出来的学生或者教官。
这个世道,许多东西都靠不住了,但是一道扛枪加上一道念书的交情,总比其他很多东西更靠得住一些,所以这些人往往也比其他人更抱团,因而爬得更高走得更远,然后在他们身边会聚集更多的人,推着他们再上一层楼,羡煞了那些野路子出来的杂牌军官。
驻扎在衡州的那个师,听说就有云南陆军讲武堂出来的旅长、团长之类的长官,平日里很瞧不起其他那些土包子,张斗魁和附近的几伙土匪都在这几个人手里吃过亏,打不过就得想办法拉拢,可惜一直没能搭上这条线。
张斗魁和另外两名头领互相看看,不觉都两眼放光。
这个顾岳,可是现成送上门来的一条线。
张斗魁忽而想起一事:“和顾岳关在一起的那两人,是不是已经知道他是谁家的?会不会帮着这小子逃跑,好卖给顾家一个情面?”心念既生,立刻转头喝道:“山猴儿!”
白天里跟在张斗魁身边的那个瘦小劫匪应声从窗外翻了进来。
张斗魁道:“去把师爷收着的那两副铁镣铐拿来!哦,再带两个人,把师爷的竹轿子也抬过来!”
山猴儿点点头,又翻了出去,眨眼不见人影。
柴房之中,不知谁先起的头,也或许是因为他们三人都无法入睡,此时又开始了闲谈,陈大贵说起自己是峰县与阳县交界处的桐油冲人,不免问起马三元和顾岳是哪里人,私心里想着能否寻个亲戚关系出来,他们三人同陷于这囚笼之中,若是沾亲带故的话,不说能有什么实际的用处,至少心里面多一点儿安慰――大难临头,一般人总是喜欢抱团取暖兼壮胆的。
马三元是阳县桂坪人,与大明山以及峰县恰是一东一西,隔得远了去了。
顾岳道:“我家在阳县李家桥。”
马三元一怔:“哪个李家桥?”
顾岳有些疑惑:“阳县有好几个李家桥吗?”
然而马三元立刻便想明白了,几乎跳了起来:“顾兄弟,你说你是李家桥人?”
顾岳点头。
陈大贵也已经反应过来:“顾兄弟,今日你为何不对劫匪说明白你是李家桥的顾家子弟?”
顾岳茫然:“什么?”
陈大贵痛心疾首:“顾兄弟,令尊从来没有同你说起过你家里的事?”
顾岳垂下了眼帘:“先父少年从军,戎马倥偬,对家乡近年来的情形,所知不多;况且平日军务繁忙,也没有太多工夫与我细说家事。”
他的父亲,大约总以为,将来有的是时间与儿子讲述家乡的种种人事,却不知世事难料,夜长梦多,有太多事,根本来不及去做,便已经没有了机会。
马三元和陈大贵都说不出什么话来了。
生长于异乡的顾岳,似乎完全不清楚李家桥和大明山土匪那种心照不宣的互相避让,又怎么能继续责怪他,遇上劫匪时不曾表明身份、免了这一场大麻烦?
马三元与陈大贵相对唉声叹气,不知道他们两人的前景是福是祸。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只不知伤的是老虎,还是不幸被两只老虎夹在中间的倒霉鬼。
天大地大,面子最大,尤其是张斗魁这样混江湖的,不论他是否对李家桥让步低头,想必都不会希望有人事先张扬出去,结果骑虎难下。
现在他们只能希望,大明山的劫匪打算和顾家谈赎金谈条件,而不是杀了他们两人灭口以绝后患。这样的话,说不定他们两人还可以做个中间人见证人什么的,顺带送顾家一个人情。
既然已经卷进来了,马三元也就不那拘着了,不免问起顾岳在哪个学堂读书,昆明那边家里还有什么人。
在哪儿读书,顾岳倒是很镇定地说了出来,只是那镇定之中,又有着掩盖不住的骄傲与自豪,眼中闪亮,精神振奋,便是在暗夜之中,也感觉得出来。
陈大贵一听顾岳读的是什么学堂,便生了三分敬畏,外加三分艳羡。马三元虽然并不意外,也很是感叹了一会,果然如他所猜想的那样。
至于昆明那边家里还有什么人――顾岳似乎有什么顾虑,不太愿意明说,只含糊答了几句,说是家里没什么人了,所以回老家来投奔本家叔伯。
马三元觉得顾岳不是那种小心谨慎、逢人只说三分话且莫抛撒一片心的老成人,以顾岳的年纪和家境,本来也应该在学堂读书的,如今独自一人,千里迢迢地回来投奔亲友,想来确有苦衷,所以才不能说出真实情形。
这么揣度着,马三元也不好再问下去了,只同陈大贵一道,聊些阳县峰县的风土人情,因不知顾岳还有什么忌讳,连李家桥的种种传闻也不去提及了。
断断续续聊到后半夜,马三元和陈大贵已经有些捱不住了,只不敢放松心神去睡,正勉强支撑着,柴房门突然被打开了,两名劫匪端着枪站在门外,喝令马三元和陈大贵先出来,待到顾岳出来时,那两名劫匪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在马三元看来,似乎连手中的枪都抖了两下,不免猜测,这伙劫匪,是不是已经知道顾岳的来历,所以这样谨慎得几乎有些畏惧了?
另有一名劫匪举着火把站在柴房外面,张斗魁站在火把下,脸上阴晴不定,瞪着顾岳,那神情,仿佛猛虎欲噬猎物一般,让胆战心惊地站在一旁的马三元和陈大贵都哆嗦了一下。
顾岳停住了脚步。
这匪首如临大敌的慎重,并不让他意外。
张斗魁慢慢走过来,手中的盒子炮一直牢牢端着,直至抵上顾岳眉心。
山猴儿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快手快脚地将一副铁镣铐扣上了顾岳的双脚,又解了顾岳身上的麻绳,将他双手也用铁镣铐锁了,再将钥匙捧给张斗魁收好。
四周的劫匪齐齐松了一口气,收起枪来。
张斗魁也收了枪,哈哈一笑:“顾兄弟,得罪了,不是张某不讲情面,实在是顾兄弟身手不凡,让我这些兄弟们自愧不如,绑老虎不得不急啊!”
顾岳诧异地看着面前这个悍匪。缚虎不得不急,这是三国演义里面,白门楼那一节,曹操捉住吕布之后、吕布抱怨绑他的绳子太紧时,曹操说的话。真看不出,这劫匪居然还将三国读得挺熟的,顺带还小小地拍了顾岳一记,将他比做吕布这样万人敌的勇将。
能够熟读三国的劫匪……
顾岳打量张斗魁的眼神,不觉便有了变化,郑重地说道:“我明白。
第4章 盗亦有道(四)
马三元和陈大贵两人再次被关入了柴房,顾岳却被关进了堂屋东侧的小厢房里,门外与窗外都有人看守。小厢房里,有桌椅有床帐,墙角熏着缠了菖蒲的艾草,气味不那么熏人,青纱帐里还搁着把大薄扇,显见得是格外的优待。
顾岳没说什么。他现在也知道了,劫匪对着有大笔赎金可拿的肉票,那是真当金娃娃一样捧着,更何况这张斗魁似乎还很有抱负、很想拉拢他的样子。
第二天上午,张斗魁带着那个山猴儿,还有另外六名劫匪,找了一杆竹凉轿将顾岳捆上去抬着,押了马三元和陈大贵,离开了那个小山村,走了好几十里的山路,太阳西斜时,转到了山林更深处的另一个小村里。村落前的池塘边,另有一条小路,曲折延伸,消失在山林中,不知通往何方。池塘边的大柳树下,坐着个瘦骨伶仃的中年男子,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手中的白折扇,带着一脸高深莫测的微笑看着他们这一行人。
顾岳一见这人,脑子里便跳出“师爷”二字来。
果然,张斗魁抢前几步,拱手道:“莫师爷,辛苦了!”
莫师爷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折扇一收,微笑点头:“大哥也辛苦了。”
随即看向刚刚从竹凉轿上放下来、但还是戴着镣铐的顾岳,笑容变得极是和蔼可亲爱:“这就是顾小哥?坐,坐,坐下来谈,咱不跟那帮土匪计较。”
顾岳毫不在意地在他对面的石头上坐了下来。
张斗魁嘿嘿笑着,带了其他人先走了。
顾岳这才发现,原来那莫师爷的身后,老柳树的粗大斜枝上,还躺着个人,想来是这师爷的保镖之类的人物。
莫师爷敲着折扇,感慨不已地说道:“莫某当年,家破人亡,无路可走之时,受张大哥活命之恩,因此立下誓言,此生一定要为张大哥找一条出路。”
顾岳诧异地打断了他:“杀人放火受招安?宋江可没什么好下场。”
莫师爷噎了一下,很快又呵呵笑道:“这可说不好。放在古时候,走了这条道,能做宋江都很难得了。如今可不一样,关东那位张大帅,还不是胡子出身?现今可是实打实的东北王,谁又能奈何得了他?”
顾岳抿一抿嘴,一时之间,找不到反驳的话。
莫师爷拈着稀疏几缕胡须,得意洋洋地说道:“莫某仔细研读了张大帅的生平,然后为张大哥定了三条锦囊妙计。”
顾岳忽然有些想笑。他发现面前这位莫师爷,做派显然是学戏台上的诸葛亮,只是怎么看怎么像照虎画猫。
莫师爷等着顾岳追问是哪三条锦囊妙计,等了好一会,不见顾岳有所反应,只好笑眯眯地自己接了下去:“张大帅当年,虽然投身绿林,但是规矩守得好,口碑好,人缘好,所以才能得了八角台当地乡绅与商会的引荐,和官府搭上了线。张大帅又是个识时务的精明人,趁着盛京将军‘化盗为良’的东风,顺水推舟,招兵买马,作了官军的管带,就此平步青云,一路高升。所以,莫某为张大哥定的三条锦囊妙计,第一条便是:守规矩。守好了规矩,三教九流,才肯放心和你打交道。”
顾岳心中若有所动。
昨晚闲谈时,马三元和陈大贵提起张斗魁这伙劫匪时,的确也说到了这件事情,正因为此,张斗魁在大明山周围三县的口碑都挺不错,至少不是最招人恨的那一伙,很多人还觉得,给张斗魁交买路钱也不坏,总比被其他劫匪抢光甚至杀光要好得多。大明山中和山脚下的那些村子,因为得了张斗魁的庇护,免了匪害,更是将这伙劫匪看成半个自己人了。
莫师爷瞄着顾岳叹气:“也就是顾小哥这样外乡回来的人,不知内情,才会和张大哥的手下闹出误会来。”
顾岳忍不住捏了捏铁链,提醒自己不要冲口便反驳莫师爷的土匪道理。
他清了清因为久不说话而有些哑的喉咙:“第二计,又是怎样?”
莫师爷:“这第二计么,便是广结善缘。”
顾岳立刻想起他们改道茶山村的原因,不无鄙夷地打量着莫师爷:“听说你们前些日子才刚劫了省府某位要员的亲戚,招来剿匪的军队,所以才离开大明山逃到这边来?这也叫广结善缘?”
莫师爷笑得越发得意:“这善缘可不好结,那些贵人,见多识广,什么巴结的招数没见过?因此莫某只好别出心裁、出出奇兵了。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咱们送了十几个别处捉来的毛匪外加七箱土鸦片,给奉命进大明山剿匪的那位蔡团长作见面礼,那位蔡团长不费半点力气便得了军功和财物,很是领情,愿意继续和咱们打打交道;省府那位原籍衡州的高督察的门庭,有名难进,多少送礼的都被扔出来了?咱们要不是有这个误劫了高督察亲家公的机会,还真摸不着门槛。借了赔罪的理由,咱们送到高府去的礼,虽说并不比别人丰厚,因着让高督察大有颜面,到底还是送进去了,听说高督察挺满意的,觉得咱们识时务会做人,尤其是对高督察很有敬畏之心,赔罪赔得有诚意,可以另眼相看一下。”
顾岳瞠目以对。
这可真是出奇制胜的广结善缘法。
他觉得自己对面前这个乡下私塾先生一般毫不起眼的师爷,也应该另眼相看一下。
顾岳想一想,问道:“既然已经和那位蔡团长搭上线了,怎么还不回大明山?”
莫师爷摇头叹气:“交情不够啊,再说了,总不能赶在蔡团长退兵之前就回去,要给蔡团长面子不是?”
免得蔡团长对上头不好交待。
莫师爷继续摇头晃脑地说道:“咱们虽然算是搭了几条线出去,但是要谋出路,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