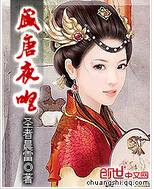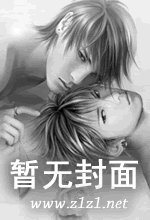盛唐贤后-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十月二十八,一封参扶风太守李渊的折子飞到了隋炀帝的案头,凑折上说太守李渊在任上不不思皇恩,政事草率,大凡有空,皆在饮酒作乐,除此之外,还有贪污受贿之行,这不,他家里妻子病得奄奄一息,他竟特意高价从外面购了两名美姬带进太守府云云……
隋炀帝接到这封折子的时候,微眯了眯眼,后不知想到什么,竟将李二郎和李建成召进宫去,将折子递给他们看,待两人看完之后,隋炀帝的目光落在这兄弟两人身上,喜怒莫辨的开口问了一句:“李大郎,李二郎,你们兄弟俩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回陛下,家父与家母一向鹣鲽情深,这折子上的事,多半是捕风捉影,还望陛下明鉴。”原本被皇帝赐了坐的李建成一听,吓得急忙起了起来,他双手揖礼,长躬于地,一脸诚惶诚恐的开口道。
“李二郎,你呢?”隋炀帝没有理会李建成,他将视线转到李二郎身上,盯着他继续问。
“我与哥哥想法一样,这写折子的人简直恶毒之极,我父与我母情深义重,朝野上下,谁人不知?陛下,不知此折为何人所写,二郎恳请与此人当面对质。”李二郎尚不是官身,他本就站着,看完奏折后黑着的一张脸听得皇帝之言后,愈发的怒了几分,但见他紧握双拳,一脸义愤填胸的开口道。
第七十章 母逝
“折子么,自然是御史写的,御史本就有望风而凑之权,你找他们也没用,好了,我找你们来也没什么大事,只因事涉你们的父亲,你们身为人子,有权力了解,现事情大概经过你们已经知道了,此事我会派人前去查证,你们先回去吧。”
“我听说,你们的母亲病情愈发的重了,让史院判随你们一同过去看看。“隋炀帝静静的看了兄弟俩一会,随后挥了挥手,让他们先行离去。
兄弟俩从贞观殿的御书房出来后,因要等皇帝的近侍帮他们去传太医院的史院判,就在御书房外的园子里站了一会,约莫站了一盏茶的功夫,史院判还没到,却碰到了由此路过的如意公主,如意公主不知是要去找皇帝还是准备去皇后的寝宫,她看到李二郎之后,顿时停住脚步,转向朝他走了过来:“李二郎,我听说表婶病得很重,最近可有好转?“
“回公主,家母病情尚未好转。“李二郎开口答道。
如意正要答话,却见父皇身边的福公公带着背着药箱朝这边走过来的史院判,她眼珠微微一转,到唇边的话咽了回去,转而开口道:“李二郎,这史院判是父皇喧来随你出宫去为表婶看诊的吧?我听说表婶病了,原本就打算这两日去看她,现既在这里碰上你们,正好随你们一同过去罢。”
李二郎看了她一眼,并未言语,李建成生怕公主责怪自己兄弟无礼,忙接了一句:“公主能有此心,我等自是欢迎感念之极。”
“谢谢大表兄,李二郎,你看到没有,大表兄可是比你客气多了。”如意听眉眼一弯,先朝李建成道了句谢,随即又转目瞪了李二郎一眼,就这样,李建成兄弟从皇宫回来的时候,不仅带来了史院判,身边还跟着如意公主。
如意在李家兄妹面前虽从未摆过公主架子,可她究竟是公主,还是极受帝后宠爱的嫡出公主,除了窦氏昏睡在床上不能起身之后,府里的其它人听说公主来了,都过来和她见礼,如意从小喜欢跟着李秀宁跑,窦氏待她不错,她与窦氏颇有几分感情。
进入病房,瞧着病床上瘦得眼窝都整个陷下去的窦氏,她心里也颇不受好,她默默的站在一旁,看着史院判为窦氏诊脉,虽说李家兄弟心里都对母亲的病情有数,如今看到史院正,心里却仍不由自主的浮出一线希望,待史院正收回诊脉的手掌后,李二郎第一个忍不住,一脸急切的看着他问了一句:“史院判,我,我母亲怎么样?”
史院判没有回话,只微微摇了摇头,随后默默走了出去,李家诸人瞧着他这般模样,只觉整颗心都凉了下去,李建成是老大,到底老成一些,心里再难受也不能怠慢了人家院判,眼见史院判离开,连忙抬步跟了出来,如意瞧了瞧背着药箱离开的史院判,又瞧了瞧李家众人的脸色,也跟着走了出去。
“大郎君,不必相送,我自己回宫即可。”走到院外,史院判转首对送他出来的李建成拱手道了一句,他过来的时候,是宫里的马车送出来的,现马车就停在李府门外。
“无妨,我送史院判上车吧。”李建成摇了摇头,送到门外,待史院判上了马车,李建成又和如意公主告别,这才转身回府。
“史院判,国公夫人的病真的没办法医治了么?”从李府离开,原本正要和史院判分道扬镳的如意突然勒住缰绳,策马来到史院判的马车边上,出言问了一句。
“国公夫人元气已经耗尽,如今不过全凭一口气吊着,任谁都无力回天了。“史院正叹了口气道,如意听得怔住,她不由自主的想到了李二郎,李二郎是极为尊爱他母情的,如果窦氏真的……意念落到这里,如意心头分外烦躁,她手中缰绳一抖,挥手重重在马背上抽了一鞭,胯下骏马长嘶一声,荡开四蹄,朝前冲了出去……
十一月初三,已连续昏迷三日的窦氏清醒了一会,她看着一众围床边,熬得双目通红的儿女,唇边扯出一个虚弱的微笑,她目光缓缓从众人脸上扫过,最后落在脑子不太好使,此时正趴在床头,眼神像小狗般望着自己三子玄霸,眼眶一涩,几若落泪,她缓缓抬起手,轻轻抚了抚儿子的脑袋,轻声开口道:“玄霸,以后阿娘不在,你要好生听大兄和二兄的话,知道么?”
“阿娘。”玄霸脑袋向旁挪动了一下,伸出手掌紧紧回握住母亲枯瘦的手掌,一脸固执的看着她轻唤了一句,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二郎,玄霸一向亲近你,以后,他就劳你和二娘好生照顾。”窦氏不敢看儿子的目光,她垂下视线,过了半晌,复抬起视线,朝李二郎夫妇看了过去。
“阿娘,我会照顾弟弟的。”李二郎鼻子眼眶都红成一片,却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
“我也一样。”长孙小娘子跟着丈夫一起点了点头。
窦氏脸上露出一个释然的笑容,随后又将视线转到了幼子和长子身上,看着不过十岁稚龄的幼子,窦氏心头不由升起一丝歉疚,元吉虽是她的幼子,可窦氏因三子脑子有毛病之故,心里惦念最多的就是他,对幼子的管教和关心反不如三子。
“阿娘,我会听大哥和二哥的话的。”元吉迎着母亲的目光,忙开口道。
“阿娘,我会好生照顾三弟和四弟的。”李建成也跟着开口。
“阿娘相信你们,你们都是阿娘的好孩子,秀宁,你刚有身孕,不宜过多呆在病房,你……”窦氏得到幼子和长子的回答,目光又从建成元吉身上移到女儿秀宁身上,李秀宁默默的看着母亲,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般不断的往下流,面对母亲的目光,她根本说不出话来,只能一个劲的点头……
次日一早,李府传来噩耗,国公夫人窦氏病逝,全府上下升起白幡,李家兄弟伤心欲绝,李秀宁哭晕在母亲床边,被人送到她未出嫁前的院子里,她醒来之后爬起来就要去看母亲,却被赶来的李二郎给劝住。
以李秀宁的倔强脾气,窦氏不在之后,能劝住她的人还真不多,而李二郎恰好是其中一个,李二郎在母亲病重那几日显得极为脆弱,现在事真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他骨子里的果断和担当反而被彻底激发出来,他收起悲伤和眼泪,默默的与兄长一起操办着一切……45
第七十一章 乱起
大业十年,是大隋王朝正式开始走向崩溃的一年,自大业七年起,大隋天下便狼烟四起,无数不堪重赋的百姓弃耕而逃,聚啸山林,一时之间匪患四起,各地驻军为剿匪一事绞尽脑计,到了大业九年,这个矛盾进一步加剧,不仅民间匪患沸腾,就连深受皇帝宠信、在大后方为皇帝亲征高丽的大军供应粮草的楚国公杨玄感也在洛阳公然竖起了反旗。
不过此时的隋炀帝在军中积威甚重,军政大权大部份仍在他的掌握之中,得知杨玄感造反的消息之后,隋炀帝当机立断,放弃攻打高丽,转道回府,在返程的途中,调兵遣将,以风雷不及迅耳之势击败了杨玄感。
接下来,是大规模的清洗,大凡与此逆案有半点牵连的从众皆处以极刑,血腥霹雳手段一时间震住了许多蠢蠢欲动的人,若隋炀帝能趋机大力整顿朝纲,一边着手回收各门阀手中的权力,一边想办法化解朝庭与百姓之间的尖锐矛盾,不再如从前那般好大喜功和激进,或许能化解大隋危机,从而让大隋天下慢慢转向良性发展。
但自认才华无双、生性骄横自大的隋炀帝显然静不下心来做这些事,这几年国政的不顺,让他的情绪变得前所未有的暴躁,他没有耐心去各大权阀斗智斗勇,同时也接受不了臣子和民众的反叛,一心认为,只要他一举拿下高丽,解决了大隋王朝卧榻帝旁的这个后患,天下臣工和百姓,自然会对他俯首听命,现在面临的一切难题皆会迎刃而解。
为此,他不听朝臣劝阻,一意孤行,不仅不想办法安抚百姓,反而一边加重税赋,一边严令各地方军剿匪,自己则重整数十万大军,决定于大业十年三月,再次亲征高丽。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衣食无忧,生活安稳是他们一生最大的追求,如果能有一口饱饭吃,谁也不愿意去干那种提着脑袋反叛朝庭的大逆不道之事,但如今的大隋天下的百姓,在朝庭各种多出牛毛的税赋之下,十个人中就有七八个食不能果腹,衣不能遮体。
隋炀帝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思减税放粮,安抚百姓,反而不管不顾的再次下令征丁加赋,这是彻底的不给百姓活路,人一旦发现自己的活路彻底被断绝,自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说百姓的心事,但说唐国公府李家,大业九年至大业十年,堪称他们府里的灾难之年,大业九年冬,国公夫人窦氏因病而逝,举府大哀,三日后,唐国公李渊从扶风赶回来为妻子操办丧事,处理完妻子的丧事后,隋炀帝以李渊在任上不思皇恩,不悌百姓,一心贪渎享乐为由,罢了他的太守一职,责令其在家自省。
大业十年二月,李渊三子玄霸突然染病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李渊一时之间苍老数岁,三子过世还没几日,未待他缓过神来,隋炀帝已决定再次自亲高丽,自己的长子和次子皆在随军之列,李渊得知此事的时候,只觉浑身的力气都被人抽干了一般……
身体一向保养得极好的李渊承受不住这接二连三的打击,病倒了,李二郎和李建成人在军中,李渊病倒了,只能是长孙小娘子和郑氏这两个儿媳尽力照应,如此病了几日后,隋炀帝突然给国公府下了一道圣谕。
圣谕的内容是皇帝此次亲征,后方的粮草统押运和统筹一应事等皆交给唐国公负责,即让李渊做那东征高丽大军的大后方粮草官,李渊怔怔的看着宣读圣谕的太监,半天没有回神,直到宣读钦使尖着声音喝了一句:“唐国公还不接旨谢恩?”
李渊被他这么一喝,顿时一个激灵,醒过神来,他先恭恭敬敬的接过圣旨,再磕头谢恩,待钦使离去后,李渊看了手中的圣旨一会,才慢慢起身,将它放进专门装圣旨的盒子里,并召来亲信,让其去军营,通知两位郎君,今晚务必回府一趟。(自皇帝下令再次亲征后,朝中一应兵将,无事皆不可离开军营。)
也不知是不是被刺激得大了些,这些日子一直病歪歪的李渊,竟然比往日精神了许多,等傍晚时分,在军营里的两个儿子回来后,李渊立即将他们召到了书房,李渊的目光在两个儿子身上转了一转,开口道:“建成,二郎,今日为父被陛下任命为此次东征的粮草主官一事,你们都知道了吧?”
“听说了。”李建成和李二郎同时点了点头,兄弟两人的脸上都颇为憔悴,尤其是李二郎,整个人瞧上去憔悴的不像样,他和李玄霸感情极深,母亲临终前更是将其托付给自己照顾,结果母亲才走几个月,三弟也……
“你们对此有何看法?”李渊又道。
“父亲,陛下把我和二弟同时带在身边,又任命父亲为粮草官,一是认为当今朝堂能胜任此职之人的除了父亲外,其它人选不多;二则是有我们与大军在一起,也不担心父亲不尽力,依儿子看来,此倒不失为一件好事,只要父亲这差事办得好,陛下心里即便仍放不下对父亲的猜忌,庙时亦不好再公开找父亲的麻烦。“李建成迎着父亲的视线,开口道。
“二郎,你呢?””李渊对大儿子看法未置可否,他将视线到次子身上。
“父亲,若在平常时期,大哥之言自无什么不对,不过此时显然并非常时期,目前我大隋天下匪患四起,百姓早已不负重赋,陛下这个时候下令亲征,再次加赋,只怕会加剧已呈沸腾之势的民怨,父亲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粮草官,行事实在是左右为难,一个不慎,就会被扣上一顶办事不力,或被推出来为替罪羊。”李二郎显然没有兄长那般乐观,他拧着眉开口道。
李建成听得双眉一皱,下意识的就想反驳,不过他到底不是无能之辈,细细想了一下朝庭当前的局面,虽说他只是一介小小城卫官,和百姓打交道的时间并不多,并不知具体民情,却也知当今天下,百姓对朝庭确有诸多不满,到处怨声载道,这才导致匪患连连。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若是强行征粮,很容易让朝庭与百姓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从而激起民变,不强征粮,让人主动交赋的可能性不大,百姓不交这新增的税赋,粮草这一块供应不足,误了东征大军的粮草战机,那也是杀头的重罪,一念至此,他整张脸不由皱得像个包子。210
第七十二章 出征(上)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三月三十日,因东征的大军明日就要开拔,军中统帅下了一道比较人性化的谕令,大凡家在洛阳城的将士皆可回家与家人团聚一晚,次日一早来营里集合。
李建成和李二郎傍晚时分,都回到了国公府,明日就要出征,兄弟俩回府,自是要陪老父用饭,李渊现是圣命亲封的粮草统筹官,也很忙,建成兄弟俩到家的时候,李渊也刚从外面归来,他一回到家,便让人准备父子三人的晚宴。
李渊去年十一月刚丧了妻,今年二月又经历了丧子之痛,府里自不能有荤腥酒水,为此,晚宴的筹备并不繁杂,厨房里的主事是府里的老人,他根据李渊父子三人的喜好备了八道素菜,几样点心,外由李渊的贴身管家为他们准备了一壶安神去燥的好茶。
“大郎,二郎,这顿饭是为父为你们准备的践行饭,只是近几个月咱们家中事多,不宜饮酒,为父就用手中这杯清茶代酒,为你们践行,来,我们父子干一个。”待席宴摆好,父子三人入坐吃了几口菜后,李渊端手起桌上的茶杯,对两个儿子开口道。
“谢父亲。”李二郎和李建成同时站了起来,端起面前的茶水,与父亲的杯子碰了一下,随后仰头,一口喝尽的杯中之水。
李渊在两个儿子仰头的同一时间也将手中的杯子送到了自己的口边,不知是否茶水有些烫的缘故,茶水入喉的刹那间,他的鼻子莫明泛红,眼眶也跟着变得湿润起来,为了掩饰失

![[剑三]末世盛唐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41/4181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