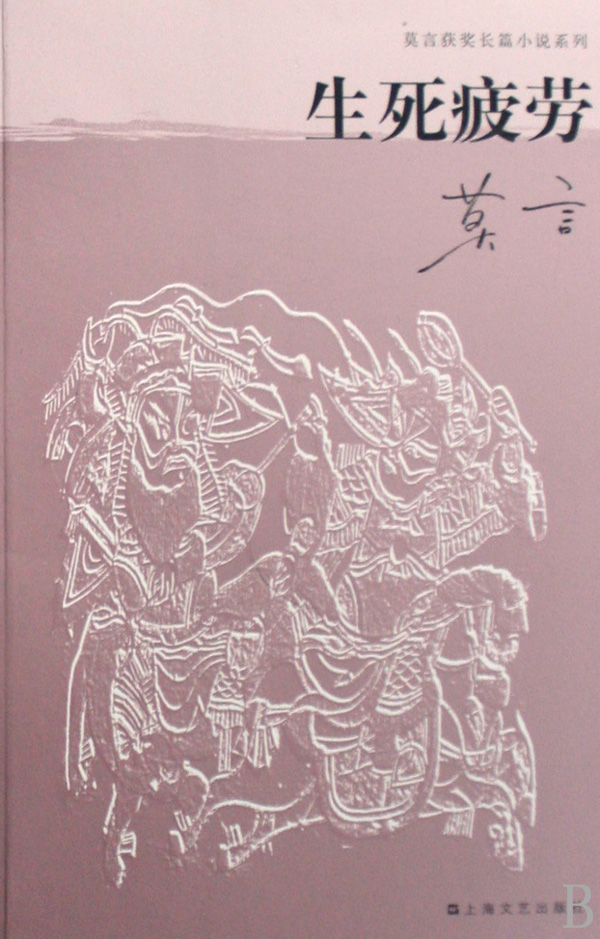生死疲劳-第6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驴店镇新任书记杜鲁文原是县供销社政工科长,我的继任者,也是我的铁哥们儿,我在长途汽车站给 他打了一个电话,求他帮我找一间僻静的房子,他略有迟疑,但最终还是答应了。我们没有坐公共汽车, 而是悄悄地溜到县城东南方向那个坐落在运粮河边的名叫鱼疃的小村庄,在河边小码头上,租了一条小木 船,顺流而下。船主是个面孔清癯的中年妇女,有两只大大的、鹿一样的眼睛,船舱里有一个一岁左右的 男孩。为了防止男孩爬出船舷,少妇用一条红布带子,一端拴着他的脚脖子,一端拴在船舱隔板的格子上 。
杜鲁文亲自开车,在驴店镇小码头上迎接我们。他把我们安排在镇供销社后院的三间房屋里。镇供销 社受个体经营者冲击,已经基本垮台,职工多半去自谋职业,只留下几个老人看守房屋。我们居住的空屋 是原供销社书记住过的,此人已进县城养老,房中一应家什俱全。杜鲁文指指那一袋子面粉、一袋子大米 、两桶食油和一些香肠、罐头之类的食品,说:“你们就在这里猫着吧,缺什么东西,往我家里打电话, 千万不要随便出来,这里是庞书记的包片,她经常搞突然袭击杀过来。”
我们开始了昏天黑地的幸福生活。我们除了做饭、吃饭,然后就是拥抱、接吻、抚摸、做爱。我不得 不惭愧但坦率地告诉你,因为我们仓惶出走,根本没带换洗衣服,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赤身luoti。赤身 luoti做爱是正常的,但当我们每人捧着一个碗,赤身luoti对坐喝粥时,荒诞和滑稽的感觉就产生了。我 自我嘲讽地对春苗说:“这里就是伊甸园。”
我们白天和黑夜不分,梦境与现实混淆。有一次,我们在做爱过程中沉沉睡去,春苗猛地推开我坐起 来,惊恐不安地说:“我梦到船上那个小男孩了,他爬到我的怀里,叫我妈妈,要吃我的奶。”
——你儿子无法抵抗庞凤凰的魅力,为了协助她去完成惩罚庞春苗的计划,他在你妻子面前撒了谎。
我追随着你与庞春苗混合在一起的那条双股绳子般的气味线,他们跟随着我,丝毫不差地沿着你们走 过的路线来到了鱼疃码头。我们上了那条小船,船主是一个生着两只鹿眼的中年妇女,船舱里拴着一个只 穿一件红兜肚的黑胖男孩。见我们上船,男孩非常兴奋。他揪住我的尾巴往嘴里塞。
“去哪里啊?”女船主站在船尾,手扶橹把,亲切地问我们,“二位同学。”
“狗,去哪里?”庞凤凰问我。
我对着大河下游吠叫两声。
“往下走。”你儿子说。
“往下走也该有个去处啊。”女船主道。
“你只管往下摇,到时候狗会告诉你的。”你儿子自信地说。
女船主笑了。船到中流,逐浪而下,犹如飞鱼。庞凤凰脱掉鞋袜,坐在船舷上,把两只脚伸到水里。 两岸浅滩上的红柳丛连绵起伏,不时有成群的鹭鸟在柳丛中飞翔。庞凤凰唱起歌来。她嗓音清脆,歌声出 喉,宛如串串银铃碰撞。你儿子嘴唇哆嗦着,偶尔也从口中进出一两个孤独的字眼。他显然也熟知庞凤凰 所唱歌曲,但是他开不了口。那男孩笑容满面,咧开已经生出四颗牙齿的嘴巴,流着口水,咿咿呀呀地跟 着唱。
我们在驴店镇小码头上了岸。庞凤凰极其大方地付了船钱。因超出原定船价太多,那鹿眼女人显得惶 惶不安。
我们准确地找到了你们藏身的地方。敲开门后,我看到你们脸上那羞愧和惊恐的表情。你狠狠地盯我 一眼,我尴尬地叫了两声。我的意思是说:蓝解放,请原谅,你已经离家出走,不再是我的主人,你儿子 才是我的主人,而执行主人的命令,是我的天职。
庞凤凰揭开一个铁皮小桶的盖子,将里边的油漆,泼在了庞春苗的身上。
“小姨,你是个大破鞋!”庞凤凰对目瞪口呆的庞春苗说罢,然后对着你儿子一挥手,像个指挥果断 的军官一样,说,“撤!”
我跟随着庞凤凰和你儿子来到镇党委驻地,找到了党委书记杜鲁文,庞凤凰用命令的口吻说:“我是 庞抗美的女儿,请你派一辆车,把我们送回县城!”
——杜鲁文来到我们的被油漆污染的“伊甸园”,支支吾吾地说:“二位,依鄙人愚见,你们还是远 走高飞吧。”
他送给我们几套换洗衣服,又拿出一个装有一千元钱的信袋,说:“不必拒绝,这是借给你们的。”
春苗圆睁着眼睛,茫然无措地望着我。
“给我十分钟,让我考虑考虑,”我向杜鲁文要了一根烟,坐在椅子上,慢慢地抽着。烟抽到半截时 ,我站起来,说,“今晚七点,请你把我们送到胶县火车站吧。”
我们乘坐由青岛开往西安的列车,到达高密站时,已是晚上九点半钟。我们将脸贴在肮脏的车窗玻璃 上,看着站台上背着沉重包裹的旅客,还有几位神情默然的铁路员工。远处的县城灯火辉煌,车站广场上 ,许多拉客的黑车司机和卖食品的小贩在那里大声吆喝着。高密啊,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堂堂正正地回来 呢?
我们去西安投奔了莫言。他从一个作家班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小报担任记者。他把我们安排在他租居 的“河南村”一间破烂不堪的房子里,他自己去办公室睡沙发。他送给我们一盒日本产超薄避孕套,又怪 又坏地笑着说:“礼轻情意重,请笑纳!”
——暑假期间,你儿子和庞凤凰又命令我追寻你们的踪迹,我带他们到了火车站。对着一列西行的火 车我低沉地呜呜着。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的气味线,就像那两条明亮的铁轨一样,伸展到遥远的、我的嗅 觉无能为力之地。
第五十一章西门欢县城称霸蓝开放切指试发
1996年暑假,你们逃亡已经五周年。你在莫言担任总编室主任的那家小报当编辑、庞春苗在小报食堂 当炊事员的消息,早就传到了你妻子、你儿子的耳朵,但他们好像把你们彻底遗忘了。你妻子继续着她炸 油条的工作并保持着她吃油条的爱好,你儿子已经是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学习成绩优良。庞凤凰 和西门欢也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他和她中考成绩都很差,但一个是县里最高领导的女儿,一个是拿出五 十万元为第一中学设立了“金龙奖学金”的大款的儿子,即便他们考零分,第一中学的校门也为他们敞开 着。
从初中开始,西门欢就来到县城就读,他的母亲黄互助也跟来县城,照料他的生活。他们住在你的家 中,使这个寂寞冷清的院落,热闹了许多,甚至热闹得有些过分。
西门欢天生不是个读书的孩子,他在这五年里做过的坏事难以尽数。进县城第一年他还有所收敛,从 第二年开始,他就成了南关一霸,他与北关刘小罗锅、东关王铁头、西关于干巴坏名相齐,是县公安局都 挂了号的“四小恶棍”之一。西门欢尽管干尽了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所能干的一切坏事——许多应该是成年 人干的坏事他也干了——但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坏孩子。他身上永远穿着漂亮、合体的名牌服装 ,身上永远散发着清新爽朗的气味。他的小头永远理得短短的,小脸永远洗得白白的,唇上黑油油的小胡 子标志着他的青春年少,连小时有些斗(又鸟)的眼神也得到了矫正。他待人接物一团和气,满嘴甜言蜜语 ,对待你的妻子更是礼貌有加,一口一个小姨,叫得十分亲热。所以,当你儿子对你妻子说:“妈,你把 欢欢撵走吧,他是个坏孩子。”
你妻子却替西门欢说话:“他不是挺好吗?他处世活络,会说话,学习成绩不好,那是个人天分有限 。我看他将来比你吃得开,你就像你那个爹,一天到晚闷着头,好像全中国的人都欠你们的钱。”
“妈,你不了解他,他会伪装!”
“开放,”你妻子说,“即便他真是个坏孩子,他闯了祸也有他爹帮他收拾,用不着咱管。再说,我 跟你大姨是亲姊热妹,一胞双胎,我怎么能开口赶她们走?熬着吧,再熬几年,等你们高中毕业,就各奔 前程了,那时,即便咱留他,人家还不一定住呢!你大伯那么有钱,在县城置一套房子,那还不是小菜一 碟?住在咱家,是为了彼此有个照应,这也是你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意思。”
你妻子用许多难以辩驳的理由,否定了你儿子的建议。
西门欢所干坏事,可以瞒过你的妻子,可以瞒过他的母亲,可以瞒过你的儿子,但瞒不了我的鼻子。 我是一条十三岁的狗,嗅觉已经退化,但辨别身边人的气味及他们留在各处的气味还是绰绰有余。顺便说 一句,我已经让出了县城狗协会会长的位置,接替我的,是一条名叫“阿黑”的德国种黑背狼犬,在县城 的狗世界里,黑背狼犬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退位之后,我已经很少参加天花广场上的圆月例会,偶尔参 加一次,也感到索然无味。我们当年的圆月例会,总是载歌载舞,总是喝酒吃肉,总是恋爱交配,可现在 的年轻一辈,它们的行为,不可理喻匪夷所思。譬如,有一次,阿黑亲自动员我去参加一次它所说的最刺 激、最神秘、最浪漫的活动。我被它的盛情所动,准时到达天花广场。我看到数百条狗从四面八方狂奔而 至,没有寒暄客套,没有打情骂俏,仿佛谁也不认识谁一样,大家围着那个重新竖立起来的断臂维纳斯雕 像,仰起头,齐吠三声,然后调头狂奔而去,包括狗协会主席阿黑也是这样。真是来如闪电去似疾风,片 刻之后,便把我孤零零地闪落在遍地月光的广场上。我望着那闪烁着幽蓝光辉的维纳斯,直怀疑自己是在 做梦。后来我听说,它们玩的是最时髦、最酷的“快闪”游戏,参加游戏的狗,都自称为“快闪一族”。 听说他们后来还玩了一些更加莫名其妙的行动,但我都没有参加。我已经感觉到,我狗小四管领风骚的时 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充满了刺激和狂想的时代已经开始。狗的世界如此,人的世界也大致相 同。尽管此时庞抗美还在位上,并盛传她即将升到省城担任要职,但距离她被纪委“双规”、“双规”后 被检察院立案、最后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已经为时不远。
你儿子考入高中后,我不再担当接送他上学的任务。我本可以每天卧在西厢房里,睡睡懒觉,回忆一 下往事,但我不愿意,因为这样会加速我肢体和大脑的老化。你儿子不需要我了,我就每天跟随你妻子到 火车站广场上去看她炸、卖油条。就是在这里,我嗅到了车站广场周围的那些发廊、小旅店和小酒馆里, 经常地留下西门欢的气味。这小子伪装成背着书包上学堂的乖乖仔,但一出家门就会搭上一辆专门在路口 等候着他的“摩的”,直奔车站广场。开“摩的”的是一个满脸络腮胡须的彪形大汉,他心甘情愿地做一 个中学生的专门车夫,西门欢的出手大方显然是主要原因。这里是“四小恶棍”共同拥有的地盘,也是他 们吃喝嫖赌的地方。这四个小恶棍的关系,像六月的天气一样变幻不定。他们时而好得如同亲兄奶弟,在 酒馆里猜拳行令,在发廊里玩弄野“(又鸟)”,在旅店里搓麻抽烟,在广场上勾肩搭背,如同四只用绳索 连络在一起的螃蟹。时而又翻脸无情,分成两派,像乌眼(又鸟)一样死啄。有时候也出现三个打一个的局 面。后来,他们又各自发展了一帮小兄弟,形成了四个小团伙,小团伙的关系也是时分时合,车站广场周 围,被他们闹得乌烟瘴气。
我与你妻子,亲眼目睹了他们之间一次惨烈的械斗,但你妻子并不知道械斗的总指挥是她心目中的好 孩子西门欢。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正所谓光天化日之下,先是广场南侧那家名叫“好再来”的酒馆 里,传出了吵嚷喧闹之声,接着有四个头破血流的小青年从酒馆里逃出来,后面有七个手持棍棒、一个拖 着墩布的小青年追赶出来。那四个小青年绕着广场逃窜,他们虽然头脸上受了伤,但似乎并没有恐惧与痛 苦。那些追赶者们,脸上也没有凶煞之气,有几个脸上还带着傻呵呵的笑容。这场械斗在初发阶段看上去 竞像一场游戏。四个逃跑者中有一个身材瘦高、脑袋呈长方形、如同旧时更夫打更所用梆子的,正是西关 的小恶人于干巴。他们四个并不完全是逃窜,他们在逃窜过程中还发起了一次反冲锋。于干巴从怀中掏出 一把三角刮刀,显示出他在四人当中的首领地位,他那三个小兄弟,则从腰间抽下皮带挥舞着,“呀呀” 地呐喊着,跟着于干巴冲进追赶者群中。一时间,棍棒打在头颅上,皮带抽在腮帮子上,喊叫声与惨叫声 纠缠在一起,场面十分混乱。广场上的人纷纷逃避,接到报警的警察还在途中。这时,我看到于干巴将他 手中的刮刀捅进了那个挥舞着墩布的小胖子的肚子,那小胖子惨叫倒地。见同伴受了重伤,追赶者的队伍 顷刻瓦解。于干巴用受伤的小胖子的衣服擦干刮刀,一声呼哨,率领着那三个小兄弟沿着广场西侧往南奔 跑。
两拨恶少在广场上追逐打斗时,我看到,在“好再来”酒馆隔壁的“仙人居”酒馆里,一张靠窗的桌 子边,西门欢戴着墨镜,坐在那里悠闲地抽烟。你妻子只是胆战心惊地看着广场上的械斗,根本没发现西 门欢。即便是看到了西门欢的人,也想不到这个白脸的小青年会是这场械斗的总指挥。他从裤兜里摸出当 时颇为新潮的拉盖手机,揿了一下,举到嘴边,说了几句话,然后又坐下抽烟。他抽烟的姿势老练而优雅 ,很有港台警匪片中那些黑社会老大的风度。与此同时,于干巴率着他的小兄弟已经拐进车站广场西南部 的新民二巷,一辆飞驰而来的“摩的”与于干巴迎面相撞,驾车的正是那个络腮胡须的大汉。于干巴的身 体轻飘飘地飞到路边,远远看过去,他的身体仿佛不是血肉之躯,而是一块套着衣裳的泡沫塑料。这是一 场交通事故,责任全在于干巴。这也可以说成是一次急中生智、见义勇为、不怕牺牲自己勇撞恶棍的英雄 壮举。“摩的”翻倒在地,往前滑行出十几米,络腮胡子也受了重伤。这时,我看到西门欢站起来,背起 书包,走出酒馆,吹着口哨,追踢着一个干瘪苹果,向学校的方向走去。
我还想对你讲述西门欢因为打架斗殴被车站派出所拘留三天放出来之后,发生在你家院子里的情景。
黄互助怒容满面,撕扯着西门欢的衣裳,晃动着西门欢的身体,痛不欲生地说:“欢欢啊欢欢,你真 让我失望,我花了这么大的精力,自己什么都不干了,来陪着你、伺候你上学;你爸爸不惜血本,对你有 求必应,供给你上学;可是你竟然……”
黄互助说着,泪水就流了出来。西门欢极其冷静地拍拍她的肩膀,坦然地说:“妈妈,擦干眼泪,不 要哭,事情不像您想象的那样,我没干什么坏事,我是被他们冤枉了,你看看我这样,像个坏孩子吗?妈 妈,我不是坏孩子,我是一个好孩子!”
这个好孩子接着便在院子里又唱又跳,伪装出种种天真无邪的姿态,把黄互助逗引得破涕为笑,把我 折磨得牙酸肉麻。
闻讯赶来的西门金龙起初也是怒气冲冲,但在西门欢的花言巧语下脸上也出现了笑意。我已经好久没 见到西门金龙了,这次见到,顿感岁月
![生死河 作者:蔡骏[出书版]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