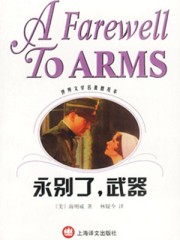永别了,古利萨雷-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温暖了。所以,溜蹄马 就喜欢在路上碰上这个女人。
可是马怎么能知道,农庄的生活有多艰难,劳动日差不多分文不付; 它又怎能知道,监察委员塔纳巴伊·巴卡索夫在办事处一再质问:事情怎么 会搞成这个样子的?到底哪年哪月才能过上好日子,到时候能对国家有所贡 献,让大家不白白劳动呢?
去年粮食歉收,饲料不足;而今年,为了让全区不丢脸,竟把超产的 粮食和牲口替别的农庄上缴了。往后怎么办,在员指靠什么,这些就不得而 知了。岁月匆匆,关于战争,人们渐渐淡忘了,而生活却依然如故:从自留 的菜园子里收点东西,要不就打点主意从地里捞点什么回来。集体农庄一文 不名;粮食、『乳』类、肉,样样亏损。夏天,牲畜大量繁殖;到了冬天,一切 化为乌有:牲口一批批饿死冻死。应该及早盖起马棚和牛栏,建立起饲料基 地,可是建筑材料没有着落,谁也不批货。至于住房,经过这些年的战争, 早就破烂不堪了。要说有人盖上新房,那准是那帮成天跑自由市场贩卖牲口 和土豆的人。
这号人现在成了气候,连建筑材料他们也能从后门搞到手。
“不,不应当这样。同志们,这不正常,这里头有『毛』病。”塔纳巴伊说, “我就不信,事情该是这样。要么是我们不会干活,要么是你们领导无方。”
“什么不应当这样?什么领导无方?”会计塞给他一叠单子,“你瞧瞧这 些计划……这是收入,这是支出,这是借方,这是贷方,这是差额。没有盈 利,只有亏损。你还要什么?你可以从头到尾查一直。就你是『共产』党员,我 们都是人民的敌人,是这样吗?”
有人『插』话了,于是吵吵嚷嚷,大家争论不休。塔纳巴伊抱着脑袋坐在 那里。他在苦苦思索,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为集体农庄感到痛心,不仅 因为他在农庄劳动,——还有别的一些特殊的原因。有人眼塔纳巴伊有宿怨。 他清楚,现在这些人在背地里讥笑他,要是遇见他,总是挑衅地盯着他的脸, 仿佛说;喂,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你还要来一次没收富农的财产?只是眼下 我们的油水不大了。你在哪儿爬上去的,还从哪儿给滚下来。咳,怎么在火 线上没有把你打死了呢!……
他只是刮目相看:等着瞧吧,混蛋们,反正得照我们的主意办事!可 是这些人又不是异己分子,都是自己人。就拿他的哥哥库鲁巴伊来说吧,现 在他已经上了年纪了,战前在西伯利亚蹲了七年。他的儿子部长大了,个个 跟父亲一样,把塔纳巴伊恨死了。是呀,他们凭什么得喜欢他呢?说不定他 们的子子孙孙都要同塔纳巴伊一家结下不解之仇。
这也是事出有因的。事过境迁,可人们的怨气没消。过去那样对待库 鲁巴伊对不对呢?难道他不就是个勤俭持家的当家人,一个中农吗?手足情 谊又在哪儿呢?库鲁巴伊是前妻生的,而他是后妻生的,可是用吉尔吉斯的 风俗,这样的兄弟等于一个娘肚子里生的。
这么说,他是六亲不认了,那阵子有多少流言蜚语啊!现在,当然罗, 可以重新评说评说。可当时呢?难道不是为了集体农庄他才这么干的吗?这 么做对不对呢?过去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可是经过一场战争,有时候就不这 么想了。对个人,对集体农庄,这样做是不是要求过多了呢?
“哎,你怎么老坐着,塔纳巴伊,你倒是说话呀!”人们让他继续参加讨 论。于是,还是那些事情:冬天得把各家院里的粪肥收集起来,送到地里; 大车没有轮子,这么说,得买点榆木,买点铁皮,做几个木头轮子。可哪儿 来这笔钱呢?立个什么名目,会不会给点贷款呢?银行可不信空话。旧渠得 整修,还得挖新渠,这工程又大又难。冬天大家没法出工,因为地上了冻, 上是创不动的。等开了春,活儿就应接不暇了:得播种,接羔,间苗,还得 割草……畜牧业怎么办?接羔的房子在哪儿?『奶』厂的情况也不妙;牛圈的顶 棚精烂了,饲料不够吃,『奶』牛不出『奶』。一天到晚讨论来讨论去,结果又怎么 样呢?有多少火烧眉『毛』的事要办,有多少困难和不足呵!有时候一想起来都 叫人寒心。
但还是鼓起勇气,把这些问题重又提到党组会议和农庄管理委员会上 进行了讨论。
『主席』是乔罗。后来只有塔纳巴伊才看重他。批评起来当然容易得多。 塔纳巴伊管的只最一群马,而乔罗,对农庄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得负 责。是的,乔罗是个硬汉子。
有时候,看起来事情搞得一团糟:在区里,有人冲着他敲桌子;在农 庄,有人揪住他的胸脯不放。遇上这种种情况,乔罗却从来也没有灰心丧气。 处在他的地位,塔纳巴伊导就得发疯,要不就得上吊了。而乔罗,却照样管 着农庄的事务,坚守岗位,一直到后来心脏病太严重了,还担任了两年多的 党支部书记。乔罗善于跟别人谈心,鼓起对方的信心。结果常常是,听了他 的话,塔纳巴伊重又相信一切都会好转,相信总有一天会过上好日子,正如 革命刚开始时人人盼望的那样。只有一次,他对乔罗的信任发生了动摇,不 过那一次,也多半是他自己的过错……
溜蹄马当然不清楚塔纳巴伊心里在想什么,它只见到他从办事处出来, 皱着眉头,怒气冲冲的。他猛地跳上马鞍,狠劲地扯着缰绳。溜蹄马觉得出 来,主人心情很坏。尽管塔纳巴伊从来没有打过它,但是碰到这种时刻,溜 蹄马还是怕它的主人。要是在路上遇到那个女人,马就知道,主人的心情准 会好转,他会和气起来,会轻轻勒住它,会跟她悄声细语地说起话来,而她 的手就会在古利萨雷的鬃『毛』上路来路去,搂搂它的脖子。
谁的手也没有她的手那样柔软。这是一双奇妙的手,那么富有弹『性』, 那么敏感,如同那匹额际长着一颗星星的小红马的嘴唇一样。世界上没有一 个人的眼睛能同她的相比。塔纳巴伊微微欠着身子跟她说着话,而她,一会 儿笑逐颜开,一会儿又满脸愁云,摇着头,不同意他说的什么话。她的一双 眼睛,忽儿闪亮,忽儿发黑,恰似月『色』下湍急的溪水底下的石子。分手的时 候,她总是频频回顾,不断地摇头叹息。
这之后,塔纳巴伊一路上便陷入沉思。他松开缰绳,于是溜蹄马就随 心所欲地、自由自在地小步跑着。马鞍上好象没有主人似的;无论是他,无 论是马,好象都出神火化了似的;好象歌声也是自然流『露』似的。轻轻地,含 混地,伴随着古利萨雷富有节奏的马蹄声,塔纳巴伊在哼着歌子,唱着先人 们的痛苦和忧伤。而溜蹄马,选了一条熟悉的小径,驮着他,涉过小河,进 了草原,因到马群那里……
古利萨雷喜欢主人这时的心情,它按照自己独特的方式也喜欢这个女 人。它能认出她的体态,认出她走路的姿势,凭它灵敏的嗅觉,甚至能闻出 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奇异的花香——那是丁香花的香味。她的脖子上挂着 一串用于丁香花劳穿起来的项链。
“你瞧,它多么喜欢你,贝贝桑。”塔纳巴伊对她说,“你好好『摸』『摸』它, 多『摸』『摸』。
瞧,它竖着耳朵听着响。简直象头牛犊子。有了它,现在马群不得安 生了。你要是放任不管,它就跟公马咬架,象狗似的。现在只好把它骑出来, 我都担心,会不舍伤了它的筋骨。还大娇嫩呢。”
“是呀,它倒是喜欢的。”她若有所思地回答说。
“你是想说,旁人不喜欢?”
“我本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都不是那种谈情说爱的年龄了。我挺可怜 你。”
“那是为什么?”
“你不是那种人。往后你会痛苦的。”
“那你呢?”
“我算什么?——一个大兵的老婆,寡『妇』。而你……”
“我,是监察委员。这会儿路上碰见了你,有几件事向你调查调查。”塔 纳巴伊想开个玩笑。
“你怎么老是在调查情况呢,小心点。”
“哎,我这又怎么啦?这不是——我走我的服你走你的路。”
“我是走我的路,咱们俩走的不是一条道。好吧,再见了。我没工夫。”
“你听着,贝贝桑!”
“什么呀?别这样,塔纳巴伊。何苦呢?你是聪明人。没有你,我已经 够受的了。”
“怎么啦,我是你的仇人还是怎么的?”
“你这是跟自己过不去。”
“怎么理解呢?”
“随你的便。”
她走了,而塔纳巴伊骑着马在大街上走着,装成去什么地方办事的样 子。他拐个弯,朝磨坊或学校的方向走去,兜了个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 方,为的是哪怕能远远地再看望一番。看着她从婆婆家走出来(上工的时候, 她把女儿放在那里),牵着小姑娘的手,朝村子尽头的家院走去。她身上的 一切,包括她那种竭力不朝他这边张望、径直走路的样子,她那黑头巾下白 净净的脸,她的小闺女,还有旁边跑着的小狗,——所有这一切,他都感到 无比的亲切。
最后,她进了院子,消失不见了。这时候,他才朝前赶路。一路上他 想象着:她如何开了门,进了空『荡』『荡』的家,如何脱下破旧的棉外套,只穿一 件连衣裙跑去打水,如何生了火,给小姑娘梳洗、喂饭,如何从牛群里接回 母牛,最后,到了夜里,如何孤单单地躺在黑漆漆的、冷清清的屋里,反反 复复地说服自己,也说服他:他们两人无法相爱,他是个拖家带口的人,在 他这样的年龄还爱上别人未免可笑,什么事情都得适可而止,他的妻子是个 好人,所以更不应当使她的丈夫再为别的女人烦恼。
塔纳巴伊思绪万千,很不自在。“看来,命中没有缘分。”他思忖着, 凝视着河那边烟雾绕绕的远方。他哼起一支支古老的曲子,把那些烦心的事; 农庄啦,孩子们的衣服鞋子啦,朋友仇人啦,已经好几年不讲话的哥哥库鲁 巴伊啦,还有那偶然梦见、但总要出一身冷汗的战争啦——把这人世间的一 切烦恼,统统抛到脑后。他暂时忘记了他经受过的一切,以致他都没有觉察 到,马正在浅滩上涉水过河,等上了岸,重又奔跑起来。
一直到溜蹄马感到近处的马群,加快了步子飞跑的时候,塔纳巴伊这 才回过神来。
“驾!古利萨雷,你这是往哪儿跑?!”塔纳巴伊如梦初醒,便抓紧了缰 绳。
第一卷 第五章
不管怎么说,那个年头无论对塔纳巴伊,还是对溜蹄马来说,都是黄 金时代。一匹千里驹的名声,不下于一个足球健将的荣誉。昨天的『毛』孩子, 成天在后院追着足球,今天忽然间变成了天之骄子,变成了行家议论的中心, 群众欢呼的对象。只要他能命中球门,他的声誉便与日俱增。后来,他渐渐 退出球场,最后被彻底遗忘。而首先把他忘记的,往往是欢呼声喊得最响的 人。一代球王终于让位于后起之秀。一匹千里马发迹的过程,也是如此。当 它在比赛中独占鳌头时,它名声四起。唯一的差别也许只在于:马是无人忌 恨的。马是不舍嫉妒马的,而人,谢天谢地,还没有学会忌很起马来。尽管, 怎么说好呢?——有了嫉妒心,就会不择手段。真有这样的情况:有人嫉妒 心太重,为了报复,竟把钉子针到对方马的蹄子里。哎哟,这可是恶毒透顶 的嫉妒心肠!……不过,这事且由它去吧!……
托尔戈伊老汉的预言实现了。这一年的春天,溜蹄马象颗明星,一跃 而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古利萨雷!”“塔纳巴 伊的溜蹄马!”“咱们村的宝贝!”……
而那些拖鼻涕的娃娃们,还没有学会发“p”这个卷舌音呢,个个学着溜 蹄马飞跑的架势,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奔来跑去,争先恐后地直嚷嚷:“我 是古利萨雷!”“不,我是古利萨雷!”“妈妈,你说,我是古利萨雷!”“驾, 冲啊!哎——,我是古利萨雷!”……
什么叫荣誉,它有多大的威力,这点溜蹄马是在它参加第一次赛马时 才有所了解的。
那天正是五一节。
群众大会之后,在河边的大片牧场上举行各种竞技比赛。无数的人群, 或步行,或骑马,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有的是从邻近的国营农场来的,有 的是从山里来的,有的甚至是从哈萨克斯坦赶来的。哈萨克人把他们的骏马 排成一溜,让大家观看欣赏。
大伙儿都说,象这样盛大的节日,在战后还是头一回哩。
一大早,塔纳巴伊就给古利萨雷备上马鞍,特别仔细地检查了马肚带, 又试了试马镫系的是不是结实。溜蹄马从他的闪光的眼睛和颤抖的双手,预 感到即将发生非同寻常的事情。主人显得十分激动。
“喂,古利萨雷,给我留神点,不许有错!”他一边给古利萨雷梳理着马 鬃和额发,一边小声地叨叨;“你听着,可不要给自己丢脸!你听着,咱们 没有这个权利!”
人们吵吵嚷嚷,跑来跑去,在这种激动不安的气氛中,感觉出人们热 切期待的心情。
邻近的几处放牧点上的牧民们,早已备好了自己的坐骑。野小子们也 都上了马,大声喊叫着,在四周穿梭似地跑来跑去。随后牧民们从四处集合 拢来,一齐向河边拥去。
牧场上人欢马叫,古利萨雷困『惑』不解。河面上空,牧场上空,河滩地 两旁的小山包上空,回响着一片笑语喧哗。那些五颜六『色』的头巾和衣裙,那 些鲜红的旗子,那些雪白的『妇』女头饰,弄得古利萨雷眼花缭『乱』。所有的马都 备上了最精巧的马具。马镫铿锵作响,马嚼子和马脖子上的小银铃清脆悦耳。
驮着骑手的群马,在队列里拥挤着,急躁不安地倒换着蹄子,创着泥 地,跃跃欲试。
几个老人——大会的裁判,在圆场上显示着矫健的骑姿。
古利萨雷感到,它的心情越来越紧张,全身的力量与时俱增。它觉得 周身火烧火燎似的,而要摆脱这种状况,就得立即冲进场地,飞奔而去。
当裁判发出进入场子的信号,塔纳巴伊使松开缰绳。溜蹄马载着他飞 到场子中央,打了个盘旋,不知往何处奔跑。两旁的人群里响起一片喊叫声:
“古利萨雷!古利萨雷!……”
凡是参加这次赛马的人,都出场了。不下五十多名骑手。
“请求人民的祝福!”大会的总指挥庄严地宣布。
剃着光头、额上缠着手巾的骑手们举起五指伸开的双手,在夹道欢呼 的人群中间走过。于是从队伍的这头到那头,响起了异口同声的祝福声:“阿 门!”于是几百双手举到额头,随后,手心贴着脸面,象一股股山涧似地落 下来。
这之后,骑手们扬鞭抖缰,飞驰而去,奔向设在九公里开外的起跑处。
与此同时,场地上开始表演各种竞技:徒步的人跟骑手角斗,骑手摔 跤,跑着马拉起地上的硬币等等。不过这些都只是开场锣鼓,好戏将在骑手 们飞驰而去的地方开始。
古利萨雷在途中急躁不安起来,它不明白为什么主人老是勒住缰绳。 周围的马欢蹦『乱』跳,神气活现。马是那么多,而且全都在飞奔疾驰,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