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车员阿姨就只是把我弄到列车员休息室,让我在里头坐着。我也听话,挎着一个小包就傻乎乎地坐着,看见她开始扫地了,我还过去帮忙。列车员阿姨连忙说:“别动别动,好好坐着,别乱跑!”我就又乖乖地坐下了。
那时从重庆到西安要坐两天火车,出门前外婆一再叮嘱:“中途在哪儿停站都别下,等所有人都下的时候你再下,那是终点站。记住,等一车的人都走的时候你再跟着走。”我懵懵懂懂地点头说好。
其实那会儿我已经明白了,尤其是一路听见广播里报站,等到听见“西安站到了”,我也就毫不迟疑地跟着下车了。但是西安站那么大,对于一个八岁的小孩儿来说,那个世界瞬间变得不知道有多大,有那么多火车来来往往,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我就记着外婆叮嘱的—跟着大人走。于是,我就跟着我们那一列车上的我认得的人走。出去以后是哪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爸妈和哥哥会来接我。
当时也就到大人屁股那么高的我,在黑咕隆咚的夜里,也不知道害怕,谁也不认识,就那么懵懵懂懂地出站了,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出站没走多远就听到了我哥叫我的声音。
暑假过完,我又按照之前来的程序,坐上回重庆的火车。想想现在的父母,之所以不敢让孩子这样出门,恐怕也是因为现在的社会治安没有当时那么好了。
西安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大雁塔、华清池、兵马俑这些著名景点我都去过,但没什么印象了,只对一顿饭印象特别深。
我第一次去西安,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父母特别高兴,带我们下馆子。那是一个国营大馆子,叫“五一饭庄”,当时是西安最高级的大饭店之一。下馆子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非常新鲜和高级的体验,因为在重庆,节俭的外婆认为下馆子是有钱人和不会过日子的人干的事儿。她什么都是买回家自己弄,把家里的伙食操办得很好,所以我在重庆就没有下过馆子。
那天在五一饭庄我和我哥一人点了一碗面,是有浇头的那种,还有两屉小笼包。那是我第一次吃小笼包,一口下去我就震惊了,完全没想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好吃的东西。回重庆之后,我对小笼包子的幸福回忆持续了将近一年。童年的我心里暗暗地想,我要是当了皇上,天天让御膳房做小笼包子给我吃!直到今天,熟悉我的朋友、同事都知道小笼包子仍然是我最爱的食物之一。
几个月前,在化妆间我偶然跟黄菡讲起这段经历,没想到她也在西安待过,家里人也带她在五一饭庄吃过饭,甚至也特别说到了那里的小笼包。更想不到的是,她在西安待的那段时间也是一九七八年。黄菡比我大四岁,当时她在西安上学,住在亲戚家。听了她的话我就想:一九七八年,一个八岁的男孩儿,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儿,互相不认识,可能在同一天,在同一家饭庄,吃着同样的东西。三十多年后,当年的两个小孩儿已是中年人,成了朋友,又同时出现在了今天的《非诚勿扰》上,这是件多么神奇的事儿啊。
5、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我在重庆的亲戚都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文化程度都不高,但都同样憨厚善良、热情好客。他们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姨婆一家,我童年欢乐的记忆有很多都出自她家。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姨婆不是外婆的亲妹妹,她们是在抗战期间逃难的路上认识并结为姐妹的,但她们一辈子比亲姐妹都亲。我们两家的关系甚至比有血缘关系的还好。
那是特别可爱而且有意思的一家人—他们家也是“母系氏族”。姨婆在印刷厂工作,是个整天乐呵呵的胖老太太,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嘴里永远都有说不完的俏皮话,她的语言似乎与生俱来地带有劳动人民草根式的幽默。她的那些话如果写出来一点儿也不好笑,但通过她的嘴,用她特有的方言和腔调说出来,就特别好笑,特别有感染力。我外公外婆的话不多,更缺乏幽默感,相比之下我姨婆是个话痨。逢年过节去他们家,从一进门开始,她就说个不停,一屋子人都被她感染了,笑个不停。
我叫姨婆的儿子“舅舅”,他和我妈一块儿长大的,一辈子都在供电局抄电表。打我记事儿开始就没听这个舅舅讲过几句话,偏偏我舅妈也是个话痨,也没什么文化,跟姨婆还特别能讲到一块儿去。她们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关系最好的婆媳。舅舅、舅妈生了一儿一女,分别是我表哥、表妹。表哥话也不多,表妹又是挺能说的人—说他们家是母系氏族真一点儿不夸张,他们家的话都让女人说了。
后来我回重庆也常到舅舅家吃饭。他爱喝酒,也能喝,他喝的酒很便宜,经常是几块钱一桶的散装高粱酒。我和舅舅喝酒的时候,就听舅妈、表妹一直不停地说,问这问那,他们家、我们家的事儿轮流说。舅舅在边上默默地坐着,隔个两分钟就端起杯子冲我说“喝一个”,一斤酒喝到底儿了,他从头到尾基本上只有这么一句话。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还有我妈在重庆电台最要好的同事黄阿姨。她是电台的资料员,前几年她去世了。我记得当时我妈接到黄阿姨女儿报丧的电话时,我正好在吃饭,看到我妈拿着电话听了没有两分钟突然放声大哭。
我小时候逢年过节有一半时间在姨婆家,另一半就在这个黄阿姨家。我从幼儿园放学回家只要妈妈不在,去的就是黄阿姨家。前面说到的,我妈和同事整夜聊天,基本上都是在黄阿姨家。黄阿姨家也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小勇,女儿叫小辉(多么朴素的名字),我们也是从小一块儿长大。后来我妈去西安了,我在重庆,只要放暑假,黄阿姨都到外婆那里把我接到她家住一阵子,每年如此。
黄阿姨话不太多,也做得一手好菜,非常贤惠,在我心目中她就是我姨妈。她老公姓陈,长相酷似朱时茂,也不怎么说话,我一直叫他陈叔叔。陈叔叔是原重庆红岩电视机厂的总工程师,我人生中第一次看电视,就是在他们家。“文革”期间上上下下都在搞运动,陈叔叔却在家里攒零件,省吃俭用,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视机,九英寸的。在当时电视机是高科技的玩意儿,放电视的时候一个院子里的邻居都聚在一起看,家里坐不下那么多人,就把电视机拿到院子里放,电线得拖得老长。黄阿姨家的院子里还有一棵黄桷树,大人们在院子里站着坐着看电视,我们这些小孩儿就爬到树上看电视。那个时候电视节目一天就播两个小时,就跟看电影一样。
现在我回重庆去,就看望两家人,一个是舅舅,一个就是黄阿姨的儿女。在我看来,黄阿姨家姐弟两个,就跟我的兄弟姐妹一样,是一家人。他们带给了我童年最为快乐和幸福的回忆。
第五章我眼中的重庆
我在重庆生活了十二年,没有生活在那里的人很难真正了解并理解它。这座城市在我看来有着非常特殊的性格,其色彩之鲜明之浓烈,超过其他很多城市,而重庆人的性格也像这座城市一样,格外地鲜明、浓烈。
1、重庆特色
重庆火锅全国闻名,但在前些年重庆市市政府曾经发布的“官方城市名片”中,排第一的不是火锅,而是美女,其次才是火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把美女排第一的道理我懂,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重庆的水土只养女人?重庆的女孩儿个子都比较高,皮肤也好—皮肤好倒可以理解,可能是在雾都终日不见阳光,有一种病态的白,打扮得也比较洋气。可为什么重庆男人的个子不高,长得也土气呢?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漂亮的女孩儿如果性格温柔,在男人看来,这就完美了,但重庆的女人大多都不那么温柔,整体性格都很泼辣。我没有一次上街不碰到重庆女孩儿吵架骂人的。而在我的印象中,一群重庆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牛,一个比一个能说,但只要有他们的女人在,就会变得都特别。重庆女人在外边基本上都会给足男人面子,随便男人怎么表现,都给他们挣面子,但是回家里以后,大多数都是女人做主。从我的家庭,到我所认识的周围的朋友、邻居家,无一不是这样阴盛阳衰。
这仿佛是重庆社会的缩影。
2、浓烈的感情
重庆人的情感特别浓烈,容易狂热。流行文化总是一阵一阵的,比如当年的呼啦圈、蝙蝠衫什么的,全国都是流行了一阵子就过,唯独在重庆流行得比其他地方都更狂热、更持久。重庆人干什么事儿,都是一窝蜂一窝蜂地去干,这跟受教育程度没什么关系,他们好像天生就是这样。
重庆人挣钱不多,但特别容易满足,尤其是通过吃饭的方式满足。他们全部的热情、精力和想象力似乎都体现在了饭桌上。每次我到舅舅家或者黄阿姨家里,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弄了一大桌好菜。一顿饭吃完,我基本上都是吃到嗓子眼儿了,两口茶刚喝下去,他们又问了:“晚上你想吃点儿什么?”真没办法。
重庆人特别热情,但似乎又太不善于表达热情,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交往后,才能感受到他们那种发自肺腑的、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热情。我的重庆朋友没有几个会说话的,尤其不善于用语言表达他们的感情,只有处的时间长了才能用心感受到。我离开多年之后回重庆见亲戚朋友,一般来说,那么多年没见面了,总会热情拥抱或者寒暄什么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表情跟昨天还见过我一样—我能理解,他们的感情都刻在心里。
3、自恋的重庆人
重庆人的性格中,我觉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自恋。他们有一种不知道来自哪里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最典型的体现是美食和方言。
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喜欢川菜和四川小吃(重庆菜也算在广义的川菜里了)。重庆人因此对他们的美食特别自恋。自恋到什么程度?只要有重庆人调到外地工作或者移居外地,重庆老乡碰到他们都会问:“那地方的菜怎么吃啊?怎么吃得下去啊?吃那些东西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啊?”并且你会发现他们在说这番话时发自内心的同情溢于言表。重庆人其实很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但他们偏偏很难接受外界的食物。在他们看来,只有吃重庆菜才能生活。我妈离开重庆都那么多年了,现在遇到重庆老乡,还是每次都会被问及上述的问题,而且你永远也不会听到重庆人夸别的地方的什么东西好吃。
这种对饮食的优越感和他们的狂热天性一样,和受教育程度没什么关系,从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全都一个样。重庆日报社、重庆电台,这都是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那里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因此我也觉得特别奇怪—难道他们没有去过重庆以外的地方吗?没有吃过川菜以外好吃的东西吗?
而说到重庆的方言,重庆人的自恋更是近乎滑稽。我至少听一百个重庆人说过:“其实我们重庆话,还是很像普通话的。”每次听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告诉他们:“我认为重庆话和普通话的区别,就像广东话和东北话的区别那么大!”而认为重庆话和普通话很像的绝不是个别人的感受,那几乎是重庆人的集体意识。我每次不赞同他们意见的时候,所有重庆人都很吃惊,这也就让我更加吃惊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被彼此震惊了。
可能会有人认为我夸大其词,你要不信,可以到重庆去,随便找个人跟他说“我认为重庆话很像普通话”,他们肯定会对你说:“对对对,你说得特别对!”
4、袍哥式义气
重庆人很江湖,特别讲义气,可能多少有些受袍哥文化影响。在很多重庆人的逻辑里是不是朋友是特别重要的标准,相比之下,是非标准反而淡一些。比如,打女人对不对?我们都会认为,怎么能打女人呢,肯定不对啊!可是到了很多重庆人那里,如果是朋友打了女人,他们会说:那也得看那女人该不该打。但如果换作不是朋友,他们会义愤填膺地说:这他妈是啥子男人哦,简直是畜生,男人啷个可以打女人呢?!
说到江湖义气,又让我想起酒。重庆人喝酒不像其他地方,你敬我一杯,我回敬一杯,我再敬你,你再敬我,如此你来我往。重庆人喝酒必划拳,输的喝。开始我很不适应这种风俗,大夏天的,十个八个朋友一桌吃火锅,又烫又辣,想喝点儿啤酒,不行,得划拳,输的才能喝。那一套划拳的酒令跟说相声一样,重庆的男女老少基本上都会。因为我刚学,划拳总是输,只能自己一杯杯地喝。几圈下来,旁边有人喊了:“哎呀,这个酒你也不能一个人喝嘛,天这么热,也让我们喝几杯嘛。”
重庆的酒令也很有意思,一套一套的,从一到九,都有说辞,说辞还很幽默,有历史,有现实,当下最流行什么,重庆人都能与时俱进地把它融入酒令里。可惜我就是学不会,也没记住。我只记得这么一段:“酒酒酒(九九九),好朋友,万事莫过杯在手,我愿长江化作酒,有朝一日跳到江里头,一个浪子一口酒。”这要用重庆话说出来会很有意思。有兴趣的朋友到重庆去玩儿,可以留意一下他们划拳的酒令,绝对是一种有趣的酒文化。
5、吃不够的小面、凉面
全国人民爱吃川菜,不仅因为它好吃,而且因为它大众。川菜的材料基本上都不算高档,大多是猪身上的东西,贵不到哪儿去。同样的钱请人吃川菜能摆一大桌,而请吃粤菜,可能就只有两道菜。
川菜让人迷恋的原因都在调料里,所以重庆有句话叫“吃的是作料”。重庆最让我魂牵梦萦的不是川菜,也不是火锅,而是路边摊上的小面和凉面。小面其实就是最普通的素面,作料是关键。我小时候的小面是六分钱一两,我一般吃二两就够了。那种味道对我来说,至今想起都是幸福的味道。
前几年回重庆,我出去逛街或者上亲戚家串门儿,回外婆家的路上是一路走着一路吃着路边的凉面回去。重庆路边摊上的凉面都是用小碗装,面很少,基本上就两筷子的,但调料放了十几样,一碗面两口就吃完了,辣得心脏都疼。我接着往前走,买一瓶冰饮料,咕嘟咕嘟喝下去。大约过十分钟心脏不疼了,嘴唇和舌头也恢复知觉了,又看到一家卖面的,再来一碗,又是两口吃下去,又辣得不行,接着再来一瓶饮料。就这样,一路走到家也吃饱了。
上次回重庆我特别想吃小面,一大清早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不停地念叨着,热情的司机为了满足我的愿望竟然带我到了机场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一家小面馆。我高兴坏了,热热乎乎的一碗小面吃下去,幸福感就在心里和胃里荡漾了一整天。
关于小面,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就算把所有的作料都原样给你,到南京就弄不出那个味道。我妈曾经多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所以现在每次有机会回重庆参加活动,主办方问我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求,我的回答全都是:有,小面!
南京也有很多种面,但那基本就是酱油面,加块大排叫大排面,加块小排叫小排面,加大肠叫大肠面,说起来有几十种,其实面都是一个味道。而重庆的面虽然就三四种,但不同的作料却调出了截然不同的口味。相比之下,南京的面条实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第六章小资本家爷爷
我爷爷很像电影《林家铺子》里的那个掌柜。爷爷是扬州邗江人,十几岁时一个人挑着担子进城当学徒,慢慢积累了本钱,后来开始自己做买卖。再后来,生意做大了,他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个钱庄。在那个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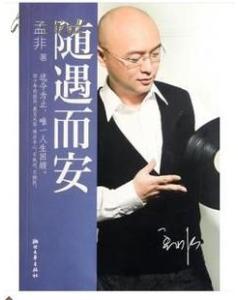
![然后,爱情随遇而安派派小说[1][1]_派派小说封面](http://www.38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