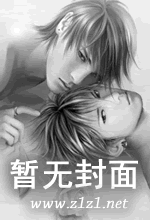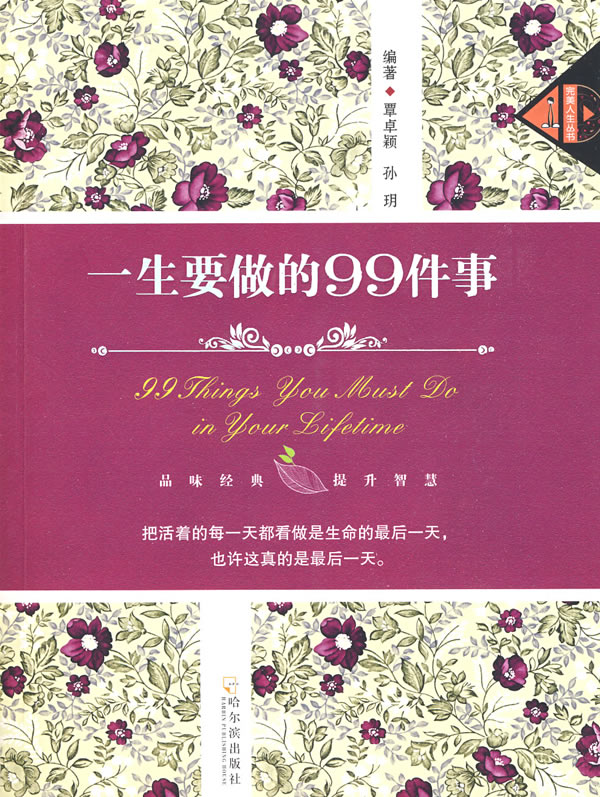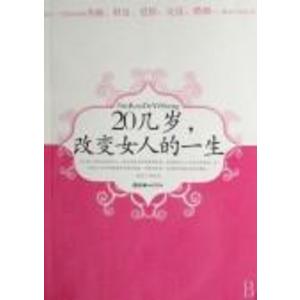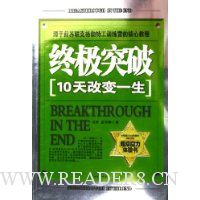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第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过《资治通鉴》,不知道神宗皇帝真的写过这篇序文,于是跑去向陈莹中兴师问罪:“神宗皇帝怎么可能写这篇东西?”陈莹中反问:“谁敢说这是假的?”林自含糊了,说:“即便是真的,也是神宗皇帝年幼时写的作文而已。”陈莹问他:“你的意思是说:天子的圣人之学不是得自天性,还有少年、成人之分?”这回,林自真的没脾气了,回去悄悄告诉蔡卞。蔡卞也不敢下手,密令太学将印版束之高阁,从此不敢再提销毁的事儿了。
苏东坡的诗文恣肆汪洋,意境高远。文人骚客们爱不释手。崇宁、大观年间,朝廷悬赏重金禁止他的诗文,最高时赏金达到八十万钱。结果,反而使苏东坡的诗文成了民间相互夸耀的宝贝。读书人如果不能背诵苏东坡的诗文,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其他人会认为此人没有品味,俗不可耐。在苏东坡的家乡四川,民间甚至流传了一句谚语,说是:“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不熟悉苏东坡诗词文章的读书人,只能吃菜根。由此可知宋徽宗君臣施政与民间舆情的反差之大。
逝者已矣,他们亲属子弟的命运则变得相当悲惨。崇宁年间,徽宗多次下诏,凡元祐党子弟,不管有无官职,均不得在京城居住,不准擅自到京师来,不准在京师及京师府界任职;后来又规定,宗室子弟不得与党人子弟联姻,已订婚尚未举行婚礼的,必须解除婚约;党人五服之内的亲属,均不得担任近卫官职。知情不报者处斩。此外,在科举考试和官吏录用晋级等方面也有不少歧视性的规定与作法。
蔡京辅佐宋徽宗出尔反尔的第二个轻佻举措,则是分门别类地治罪那些在皇帝的鼓励下,上书言事的人们。
徽宗初政时,曾经鼓励、号召天下人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结果,仅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同样言犹在耳、墨迹未干,徽宗皇帝便尽反前言,将所有奏章和上书交给蔡京父子、门客强浚明兄弟,再加上一位不错的学者叶梦得,由这个五人小组根据上述文书中的内容与词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上书言事者。
这五人“同己为正,异己为邪”,凡是与蔡京有过节的人,几乎一网打尽地被列进了“邪”字榜中。以此为发端,从此形成北宋末年的党人之祸。
在涉及到治国方略的重大事务上,徽宗皇帝的表现既轻佻又不浪漫,这种做法所伤害的远远不仅仅是上述这些被列入“邪”字榜中的人。人们有理由在这种缺少道德信念支持的变化中,感受到前景的黯淡与令人畏惧。在这两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蔡京差不多将自己的敌人和潜在敌人清除殆尽。事实上,此后二十多年的徽宗朝政,在此时已经奠定了基本的格局。
就这样,大宋帝国的元首几乎是以滑着舞步般的轻松与浪漫,处理着军国大事。此后,这种特点一再显现:在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上,缺少坚定的信念,寡谋善变,投机取巧,特别典型地表现了徽宗皇帝的轻佻。
如果说皇帝在对待元祐党人的政治立场上剧烈转变是一种政治轻佻,在治罪上书言事者上翻云覆雨是一种人格轻佻的话,那么,在他改变对上述两类人的惩治时,所表现的则是一种让人根本无法界定的轻佻。
按理说,改变对这两种人的错误惩治,应该是很受欢迎的举动。可是,徽宗皇帝在这样做时,却使人丝毫感觉不到欣慰,相反,令人对国家的前途更加沮丧与绝望。
事情的起因可能与徽宗皇帝笃信道教有密切关系。到了宋徽宗的时代,对道教的尊崇达到了一个高潮。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代帝王能够像徽宗这样崇信道教,以至于到了最后,他给自己的称号都要叫“教主道君皇帝”。
这位教主道君皇帝的神怪,与他的先祖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是端王时,就曾经有一个道士预言:“吉人当继大统”。吉人合起来,正是赵佶的佶字。赵佶当上皇帝之后,子嗣人丁不旺。道士刘混康告诉他,京城东北角风水极佳,倘若将地势增高,皇家子嗣立即便会兴旺。徽宗下令照办。不久,宫中竟然连连诞育皇子。这一来,使宋徽宗对于道教大为崇信。
有一次,宋徽宗前往圜丘祭天,蔡京的儿子蔡攸随行,由一百多个道士执仪仗为前导。队伍出了南熏门,徽宗忽然停住,指着前方的空中问蔡攸:“玉津园的东面好像有亭台楼阁,重重叠叠,那是什么地方?”蔡攸立即装神弄鬼地回答:“我只隐隐约约看见云彩间有几重楼台殿阁。再仔细看,都离地有几十丈高。”徽宗问:“看到人了吗?”蔡攸答道:“好像有一些道家童子,手持幡幢节盖,相继出现在云间,眉毛眼睛历历在目。”一君一臣,一问一答,认定了有天神下凡。于是,皇帝下令,就在其地修建道宫,名曰:迎真宫。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与皇帝相处时日最久的一个道士,名叫张虚白。徽宗皇帝从来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叫他张胡。他博学多识,精通术数,经常喝醉酒后发出预言,神奇的是每每被他言中。他曾经酒醉后枕着皇帝的膝盖大睡其觉,并且经常直言无忌地发出批评性的警告,甚至针对皇帝本人。徽宗并不计较。宣和年间,金国人俘虏了辽国皇帝天祚皇帝,派人来通告,徽宗皇帝将此事告诉了虚白。虚白的反应是:“天祚皇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候陛下,已经很久了。”此话一出,周围的人们相顾失色。天祚皇帝是公认的荒淫昏庸之君,而且亡国后成了俘虏。虚白如此比拟,完全够得上大不敬之罪,徽宗皇帝却浑然无事,手抚虚白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
1127年,徽宗皇帝真的成了亡国之君,并被金国俘虏后,又一次见到了虚白。皇帝叹息着说:“你平日所言,都应验了。我悔恨透了,没有早听你的意见。”虚白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谏。陛下好好爱惜身体吧。”据说皇帝曾经赏赐给张虚白大量财宝,虚白全部推辞不受,是一位相当懂得自爱的道士。
皇帝宠信的道士不少,像张虚白这样自爱的则不多。最有名的当属林灵素。他相貌极为奇异。据说,因为好酒贪杯,又没有钱,于是向人家赊账,欠多了酒账,债主前来讨债,他“举手自折其面”,结果,导致他一半脸干枯如骷髅,一半脸则滋润如常人。皇帝一见到林灵素,顿时就懵了,他疑疑惑惑地发问:“先生过去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我吗?”道家大师林灵素答道:“我往年在天上玉皇大帝那儿当差时,曾经侍奉过圣上您的大驾。”皇帝道:“那段事如今我还恍惚记得。我记得你好像是骑一头青牛,那青牛如今哪儿去了?”灵素回答:“我把它寄牧在外国了,不久就会来此。”皇帝又惊又喜,不但知道了自己的前世,还找到了天上的仙伴。皇帝的心情无比喜悦。
徽宗皇帝弄清楚自己的前世今生后,相当感慨。他派人宣谕有关部门:自己是上帝长子,只因为怜悯中华大地到处都是金狄之教(指佛教),因此恳求上帝父亲愿意下凡为百姓之主,令天下归于正道。于是,道箓院请示了上帝之后,正式册封徽宗皇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在此期间,道家的修行、典礼、仪式、经典与生活方式,成了皇帝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相当自觉地以此要求自己,陶醉而且乐此不疲。于是,在此期间,中国道教的势力远远压倒佛教,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顶峰。为此,道家弟子们,实在是应该感谢这位教主皇帝。
当时仅林灵素一人,就有弟子两万多人,锦衣玉食地在京城内外招摇。他的势焰极盛,甚至被人们称为“道家两府”,意思是此人的权势已经可以和宰相并列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褚慧仙卿林灵素林大师的一番做作,导致了徽宗皇帝对于元祐党人案和上书言事获罪者们的重新思考。有一天,皇帝在太清楼设宴,林灵素侍宴。恰巧太清楼下就有一块元祐党人碑。林灵素走到碑前,纳头便拜。皇帝大为讶异,问他何以如此,大师庄容回答道:“这块碑上的名字大都是天上的星宿,臣大模大样地不稽首致礼,今后回到天上,大家如何相处?”据说这位老道还随即吟诗一首: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元祐是何人?
人们找不到这位林灵素与苏东坡、黄庭坚这些人有什么瓜葛、渊源的证据。道士忽然为那些倒霉蛋说话,由不得徽宗不信。这可能是促使宋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明显好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前后,还有一位道士,也曾经以类似的方式,使皇帝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压力。据说,有一次皇帝巡视一座道观。观中的道士在皇帝面前,向上帝伏地跪拜,过了很久才起来。皇帝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这位道士回答说:“刚才到上帝办公的地方,正好赶上奎宿在向上帝汇报工作,很久才完,臣只能等他完毕才能上达奏章。”皇帝听了,感叹不已;又问那奎宿是什么人?向上帝汇报了些什么事情?道士回答:“臣离得远,听不清,对于他们谈的事情不得而知。不过那位奎宿臣倒是看清了,就是以前的端明殿学士苏轼。”据说,徽宗皇帝听了之后,大为改容。随后,对元祐党一案的态度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
在此时此刻,艺术家宋徽宗的想像则已经插上了道教的翅膀,正在现实生活中的此岸世界上空,尽情地翱翔。应该说,道家的思想观念与皇家的思想观念是最为默契的,因为两者的追求高度一致。对于道家人士来说,此岸也就是今生今世的快乐追求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长生不老,修炼成仙,白日飞升等等。如果今生今世就能够修炼成仙的话,也就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来生来世的问题。与此种聪明作法比较起来,苦巴巴地修炼来世的佛家人士,实在是显得特别愚蠢。
一般说来,皇帝内心深处最焦虑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坐稳屁股底下的这把龙椅,不要让别人抢了去;第二就是怎么样才能尽可能坐得时间长一点,最好是长生不老地永远坐下去。这两个根本性的焦虑,是大多数皇帝特别喜欢道家的主要原因。
当然,道家修炼时的美妙也实在不错。他们认为健康长寿是可以通过采阴补阳来实现的。这个过程要求:采阴的对象,最好是十六岁左右的处女;皮肤白嫩细腻,气色白里透红,骨骼玲珑细致,头发油光黑亮,五官和谐标致,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美貌处女;而且,数量越多越好。采阴的场所,最好是有山有水,林木葱茏,鸟语花香,配以潺潺流水和恰到好处袅袅不绝如缕的音乐等等。采阴的时间,最好是万物复苏的阳春时节等等。
徽宗皇帝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相当浪漫,也相当漫长。在这浪漫而漫长的过程中,宋徽宗从一位好学上进的青年皇帝,一步一步蜕化,最后,终于蜕化成了一位彻底地、昏天黑地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庸天子,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皇帝。
这个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比如:当上皇帝不久的宋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大家:“我打算在国宴上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怎么样?”
蔡京马上回答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算什么?何况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情合理。合乎情理的事情,别人说什么也就不必放在心上。”这使皇帝的感觉相当舒服。
蔡京饱读诗书,而且极有才学。他引经据典的理论阐述,可能是帮助皇帝最后解除顾虑的重要原因:他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叫做“唯王不会”。这里的“会”是会计的会。蔡京告诉皇帝:周礼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只要是君王,其花费都是不必计算、不受限制的;陛下过分节俭,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农民一样了。对于君王来说,这样做是可耻的。
这番理论,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经不能用一般的“卑鄙”、“无耻”来形容。按照儒家传统理论,逢君之恶,乃标准的奸佞之徒。不幸的是,这套理论被宋徽宗全盘接受,成为皇帝本人、他的宰相和整个徽宗一朝的基本施政纲领。
有一次,蔡京的儿子蔡攸劝皇帝:“所谓人主,就应该以四海为家,以太平岁月娱乐自己。人生几何,岂可徒自劳苦?”皇帝深以为然。转过头,在一次宫中的宴会上,对梁师成说:“先皇为天下欢乐,也为天下忧愁。如今四海太平,我才有机会放松一下,游玩游玩啊。”
梁师成回答说:“对呀。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就是陛下您这种情形呐。”这一番对话,将现实的享乐和圣人的境界联系在一起,令皇帝特别欣慰。
花石纲
中国皇家贵族、文人雅士赏玩奇石的历史相当悠久。不过,玩这么大的,徽宗皇帝可能是第一份,宋徽宗酷爱稀奇古怪的石头。按理说,一个皇帝不是喜欢肉林酒池金山银海,而是喜欢赏玩石头,这岂不是臣民的福气?谁知,皇帝的爱好和宰相的逢迎结合后,却生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怪胎。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在北宋帝国的败亡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花石纲”。
1102年,朝廷在杭州增设造作局,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工匠数千人,专为皇室制造金玉牙角竹藤织绣等物品。所需物料,全部由民间征敛。
1105年,是蔡京当上宰相的第三年。这一年,朝廷又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勔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为皇帝搜罗珍奇物品与啤颉颞异石。结果,发展为灾难性的、遍及全国规模的“花石纲”大劫难。
花石纲的本意指的是运送异石的船。当时,管成批运送的货物叫“纲”。动用大批船只向京都运送花石,每十艘船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据史书记载,起初,这种花石贡品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皇帝对这些贡品大为赞赏,进贡者纷纷加官晋爵,恩宠有加。于是,化为一道无声的号令,迅速演变成举国为之骚动。
政和年间,安徽灵壁县进贡一块巨石,高、阔均二丈有余,用大船运送到京师汴梁,拆毁了城门才算进得城中,上千人都抬不动这块大家伙。宋徽宗大喜,亲笔御书曰:“卿云万态奇峰”,并加金带一条悬挂其上。
随后,太湖鼋山又采得一石,长四丈有余,宽二丈,玲珑剔透,孔窍天成。又有一树,相传是唐代白居易手栽,故名白公桧。连石带树,预备一股脑献给皇帝。为此,特造大船两艘,花费八千贯钱才送到京师。八千贯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二百户人家的一年生活费。
华亭有一株唐朝古树,人们决定将它晋献皇帝。由于此树枝干巨大,无法通过桥梁,于是造大船海运,经楚州到开封。一日风大,树枝与风帆纠结在一起,“舟与人皆没”,一船人全部葬身鱼腹。
1123年,在太湖又采得一石,该巨石高六仞,阔需百人合抱。再造巨舰运送京城后,宋徽宗极为喜悦,赏赐搬运船夫每人金碗一只,朱勔的四个奴仆被封官,朱勔本人晋升为“威远军节度使”,那块大石头则被封为侯爵——“盘固侯”。“节度使”曾经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司令兼一省或数省的行政长官,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