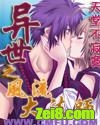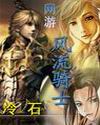朱门风流-第38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再有大约一个月,用药辅以施针,殿下的病就能痊愈了。”
听到这么言简意赅的一句话,朱高煦僵硬的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虽说此次几乎把青州城内的名医一扫而空,但那些全都是饭桶,有些人甚至看了老半天都连个病因都瞧不出来。这么个不起眼的老头倒是真有本事,几次三番用药施针,在别人看来是些小手段,可偏奏效。略一思量,他便淡淡地点了点头:“那本藩就等着一个月后。来人,送人回去。”
唐赛儿不动声色地收拾好了医箱,一如从前冯远茗那般不搭理人的架势。然而,才走到那银红大团花门帘前头,一个小太监就敏捷地撞开帘子从外头窜了进来。不用回头,她就能察觉到那人匆匆到了朱高煦榻前,凑到那位汉王耳边低声禀告了一番话。
“千岁爷,刚刚传来消息,皇上率军在宽河大捷,杀敌无数,如今捷报已经传到了京师。但是,德州、沧州、静海、天津卫,这几个地方全都加强了防卫。另外,山东都司、各卫所和千户所仿佛有些异动。至于京师……太子殿下调了大军入城,听说整个京师都戒严了!报信的人往乐安来的时候,又遇上了军中派了信使回京……”
“该死!”
朱高煦也顾不得还有外人在场,重重一拳捶在了那具梨花榻的边缘,随即怒不可遏地把榻上的所有卧具都推翻在地。那一刻,屋子里的人全都感到了那种扑面而来的怒火,顿时不敢吭声。几个当初被皇帝从身边拨过来伺候的宦官无不真切地体会到,朱高煦继承朱棣最大的一点便是那位天子不时砸下来的雷霆之怒,怪不得连这住的地方都改成了雷霆居。
唐赛儿却没兴趣杵在那里当朱高煦的出气筒,悄无声息地掀起门帘到了外头。还没出正房大门,她就听到背后传来了滚滚声浪,但这丝毫没有阻止她的脚步。
“要不是父皇这次出去只带了几万人,怎么可能还有大军可供他调动!派人给我好好地查,他这个太子居然敢擅自调兵,简直是胆大包天!他不是一直在父皇面前装老实么?这次他那层皮就该揭下来了,我要看看他怎么解释……等等,你刚刚说宽河大捷?宽河……宽河……他娘的,那不就是大宁边上?”
朱高煦气急败坏地跳下了地,眉头拧成了一团。当初还是燕王次子的时候,他就曾经领兵对抗北边的蒙元,对于大宁的状况也颇有了解,后来靖难起兵时更几乎朱棣到哪他就跟到哪,北上大宁裹挟宁王,他也有份参与,这宽河的所处位置他自是了解得清清楚楚。
“那边附近是兀良哈朵颜三卫……当初那会儿还有全宁卫会州卫新城卫,鞑靼自然不敢南下,但如今虽说大宁重建,终究不复北平行都司那般景象!倘若是鞑靼阿鲁台和兀良哈勾结,父皇又率兵北上击敌,决不会轻轻巧巧就有什么大捷,别是出了大事……没错,若非如此,那个懦夫怎么会忽然下令京师戒严各地守备!”
一下子醒悟到这最关键的一点,朱高煦顿时更加气怒,竟是赤脚下地发了好一阵火。直到枚青和王斌一同赶来时,他方才暂时息了少许火气,但仍是恨恨地说:“要是此次乃是北巡而非北征,趁着京师空虚,本藩便可以立刻北上,谅那个懦夫也没法和本藩抗衡!”
“殿下,我在京师留了些人,他们得了我的嘱咐,倘使有变就会往各家勋贵府上送信,只要有多人离心,京师便会局势不稳。”枚青如今不在京师,也说不准那儿究竟如何,只好低声劝道,“殿下暂且放宽心,须知当初太祖皇帝晏驾,皇上也没有及时得到消息,之后还不是一朝功成?殿下武勇天下无敌,皇上曾亲口称许,若真是皇上不在,这天下还不是在您指掌之中?”
这自然是赤裸裸的恭维,旁边不屑此道的王斌听得自然大皱眉头。然而,眼见朱高煦面色稍霁,他自是不会在这种时候坏人兴致,于是只默不作声。待到朱高煦问他麾下诸卫情形,他便原原本本奏报了,随即又低声说:“卑职以为,殿下确实该等一等,不得准确消息决不能轻举妄动。另外,其他的都不足虑,惟有锦衣卫无孔不入的手段不得不防。”
“本藩当然知道不能轻举妄动,都忍了这么久,不在乎一天两天!”
朱高煦口中如此说,心里却盘算着等一有准确消息便立刻率军杀将出去,只要不管三七二十一给朱高炽扣上忤逆之名,以山东到北京这么点距离,一举功成的可能性并不小。等听到最后一句,他不禁考虑了一下朱棣没死的可能性,再想想袁方,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一朝天子一朝臣,若是父皇真去了,那个袁方也就该打发去养老了,这已经是他的最好结局。换了其他人,锦衣卫不乱上一年半载就不错了,哪里能顾得上本藩?也罢,那个死胖子掌握了京师局势本藩也不怕,他活不了多久,但凡他稍有不妥,本藩便立刻取而代之!”
由于杨荣此行还带来了天子遗诏,报丧之后便拿了出来。有了这样东西,留守在京辅佐太子的所有官员不禁都松了一口大气。朱高炽当机立断,命朱瞻基精选府军前卫五千人立刻赶往大宁发丧,又连发指令调动顺天府的一应军卫,那防备何止比之前森严一倍。而朱高炽最满意的便是勋贵们毫不迟疑的态度,不但成国公朱勇调兵遣将毫不含糊,就连其他人亦是惟命是从,当天朱瞻基启程的时候,整个京畿境内已经是固若金汤。
一日之内,所有准备都已经料理得妥当,天子驾崩的消息却仍然捂得死死的——所有知道消息的人眼下都呆在了宫里,而带兵的勋贵则是各带上了两个东宫太监随行。
星夜兼程赶回来的杨荣名正言顺地留在了京师,而同样是不眠不休将近三天的张越却仍需陪着朱瞻基赶往大宁。尽管他历练的好筋骨,抵达松亭关时却感到脑袋犹如炸裂了一般,浑身上下也是疲软无力。随行的陈芜瞧见他不妥,又发现朱瞻基亦是嘴唇干裂脸色憔悴,便以此时已经过了辛时,出松亭关后不多时就要赶夜路,极其不安全为由,死活劝说在松亭关内停留一晚。松亭关守将也担心蒙人得到风声,少不得在旁帮腔,朱瞻基只得勉强答应。
张越当初第一次通过松亭关的时候,草原上还是绿草如茵,回程时却已经是陡然转冷。如今再到这里时,就只见关外已经失却了早先的鲜亮绿意,天空中满是阴霾,星星点点飘落着雪珠子。看到这种天气,他自是建议守将让人往大宁报信,到时候遣一支兵马前来会合,又强打精神到屋中陪朱瞻基说话,眼皮子却是直打架。
“原来皇爷爷在那时候还读了我的家书……说起来我这还是和你学的,那回英国公重病,你事无巨细往南京禀报,我就觉得这比空泛写些恭敬之辞恳切多了。后来我在德州病倒的那一回,你还为我代笔给皇爷爷写过家书。如今我每日习惯性地记这么些东西,这次索性就夹在问安的折子中,一并送过去了。”
“殿下居然记得这么清楚,臣当初只是觉着既是骨肉至亲,讲礼之外更需念情,没多想别的。”
“念情……不错,做人是该念情。我从小就是皇爷爷过问功课,教授骑射,跟着也不知道去过多少回军中。如今想想,皇爷爷是真的喜欢军营,哪怕是我从小就带着府军前卫演练,却不像他这么沉迷其中……皇爷爷就是皇爷爷,想学他的人不过是东施效颦而已。”
“有些事情可以仿效,有些事情却仿效不得,永乐大帝只有一个……”
朱瞻基挑了挑眉,这才若有所思地说:“大帝?我记得从前师傅提过,仿佛只有昔日孙权和唐高宗用过此号,颇有自满之意,这可不是什么好词。你这话要是让那些老臣听到了,恐怕又得编排你了!”
说完这话,他却听到了轻微的鼾声,侧头一瞧,却只见张越不知道什么时候一手支在炕桌上,已经是睡着了。旁边的陈芜见此情形忙走上前来,正要去推醒张越时,朱瞻基却站了起来,淡淡地摆了摆手说:“他在路上几天没合眼,必然是困极了,让他去睡吧。你去取一件披风来,随我去外头走走,今晚我睡不着!”
由于北平行都司已经废弃多年,哪怕重取大宁,如今的松亭关依旧是戒备森严。只是,相比从前重点防备南边,如今的重点却在于北面,所以即便是夜里,依旧能看到四处燃烧的熊熊火把,依旧能看到一队队巡逻的军士。当朱瞻基走到城头的时候,几个军官闻讯赶了过来,却被陈芜上前拦住了。
“太孙殿下眼下心情不好,你们别去扰了他。”
军官们看不见朱瞻基外袍之下的那一身麻衣,并不知道他忽然带兵前往大宁是何缘由,因此这会儿听陈芜这么一说,众人顿时偃旗息鼓。没了和皇太孙套近乎的机会固然可惜,可要是惹得这位主儿恼怒就更划不来了。于是,几个军官只得远远退开,却不敢擅离。
此时此刻天色已晚,乌云遮住了月亮和繁星,城外一片漆黑,几乎不见一丝一毫的亮光。雪仍旧是下得稀稀落落,但风却渐渐大了起来,裹挟着草原上的沙土劈头盖脸地打在人的脸上,不免有一阵阵刺痛的感觉。然而,站在大风之中的朱瞻基却是半晌都没有挪动一步,从后头看着仿佛是化成了泥雕木塑。最后,陈芜瞧着实在不对,连忙悄悄上前。
把手中另一件厚厚的白狐皮披风盖在了朱瞻基肩头,他又乍着胆子轻轻握了握这位皇太孙露在外头的手,见已经是冻僵了,他不由得暗自叫苦,忙朝身后另两个随侍的太监打了个眼色,接过了他们手中的貂鼠手套,不由分说地给朱瞻基套上了。
见人丝毫没有反应,他只得开口劝道:“殿下,就算睡不着,夜间风大,您还是进屋里眯一会吧。明日还要赶路,到了军中还要……殿下,您不会自个想想,也得想想皇上对您的期望,这冻坏了可怎么好?”
陈芜伺候朱瞻基多年,若是平日这么劝一番必定有成效,但此时此刻,朱瞻基却是压根没有理会这番话。又怕又急的陈芜眼看无用,少不得又劝了好些话,好容易才把人请回了屋子里。他也顾不得张越仍靠在炕桌上睡着,急急忙忙吩咐了人张罗送热水,待到朱瞻基坐下就亲自扒拉下了鞋袜伺候洗脚。
毫无知觉的脚也不知道被揉搓了多久,朱瞻基才发出了一声微不可闻的呻吟。他的父亲足足当了二十一年的皇太子,胆战心惊了二十一年,如今终于如愿以偿。天底下最难的就是父子君臣,以后他可也会同样如此?
第十四卷 定乾坤 第002章 忧喜参半
九月二十八日,皇太孙朱瞻基抵达大宁,即日发丧。然而,由于军中不曾准备那么多麻布,因此除了金幼孜以及张辅柳升等一些勋贵,上下将官士卒自然是没法易服。披发哭灵之后,朱瞻基便召张辅金幼孜等人吩咐回京事宜,当即议定由阳武侯薛禄守大宁,张辅柳升陈懋等于次日领军护送发灵回京。这一夜,所有人忙着诸多事宜,都是彻夜未眠。
由于快马报丧,小溪须臾便传遍了天下八方,回京这一路上,从过了松亭关开始,一路都是军民素服哭迎。那素淡的颜色再加上天地萧瑟肃杀的背景,越发流露出一种异样的悲凉来。由于是大军行进,回去这千多里路,一行人足足走了五天,每日行程不过两百多里。
这一晚是入京前的最后一夜,大军驻扎在了三河。前方早已传来消息,皇太子将率百官迎于京郊。之前虽说都是日走夜停,但上上下下的人几乎都没睡好,各有各的心事。朱瞻基自从发丧之后,除非是需要诸勋贵合议的事,其余时候一律不见外人,眼下仍然是如此。然而,柳升陈懋等人眼看京师渐近,哪里坐得住,扎营之后就聚在了一块,只派人去邀请张辅时,张辅却是借口劳累推托了。
张越这一路只是紧随着张辅。他如今却是什么都不用管了,毕竟,山陵崩这种大事压根轮不上他出面。不过,随侍张辅左右,对于这位大堂伯的审慎小心,他仍是颇为佩服。由于是护灵回京,这一路上军民上下都不忌饮食,但张辅硬是片肉不食滴酒不沾,哪怕在无人处也是一样。在如今这种天寒地冻的天气里头,能同样做到这一点的几乎再找不出一人。
这会儿看见张辅打发那前来相请的宁阳侯家奴回去,他便低声说道:“大堂伯,这一路上,随行大军正越走越少,这些人应该是被派去了北直隶南线运河一带吧?”
“汉王反意天下皆知,这时候太子殿下不防他,却是去防谁?”自打皇帝在大宁病倒,继而驾崩以后,张辅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此时脸庞消瘦了一大圈,“好在我如今和他没有瓜葛,就连遗诏也早早交给杨荣带了回去,如今掌军的又是柳升陈懋等人,想来他要打我的主意也不容易……越哥儿,幸好你提醒了一句,要是我拿着遗诏,那才是真正的烫手山芋。”
“哪里是我的劝说,大堂伯不是在拿到之前那诰书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了么?”
“那时候只是起意,但你对我说过犹不及的时候,我才真正下了决心。”张辅意味深长地看了张越一眼,见他正低头喝茶,他忍不住伸出右手拍了拍那个楠木小匣子,“我已经是食禄三千石的国公,别人不得不倚重,何必处处争先?再说,皇上之前的旨意已经明白无误地写了,说是让恬丫头长成之后,由太子殿下纳她为妃。最初成了皇妃的已经有了你姑姑,皇上既安排了恬丫头的将来,若我还霸着遗诏不放,这权臣两个字便再也脱不掉了。”
即便张辅没有明说,张越也知道他后头省略了一句话——从古至今,不想篡位的权臣几乎从来没有好下场——朱棣这辈子善待了大多数功臣,可皇太子朱高炽和勋贵之间并没有同甘共苦的感情,如今若是不知收敛,今后恐怕就苦了。虽说他隐约记得朱高炽似乎是个出了名短命的皇帝,可这种事不能对任何人说,哪怕是再亲密的人也是一样。
然而,纵使不能说,一想到王夫人膝下只有一儿一女,他却不能不为张恬着想:“大堂伯,之前那道诏书是我亲笔替皇上拟的,但我觉着此事实在是……联姻帝室固然是别人没有的荣耀,可恬妹妹毕竟还太小了。说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待到她长成之日,太子殿下也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了。须知之前杨学士金学士为先帝草拟遗诏,后宫殉葬嫔妃足有二三十人。而且,太子妃……太子妃和太子又是伉俪情深……”
“你不用说了!”
张辅一下子松开了按在那楠木匣子上的手,一下子站起身来。除了如今膝下的一儿两女之外,他之前的儿女多半是年幼夭折,对于这亲生骨肉自然是心存怜惜。然而,天子金口玉言,如今更是变成了白纸黑字,要不遵也同样是大罪。思来想去,他不由得想起了隆平侯张信那时谢绝皇帝纳己女为妃的事,可和自己身上这事一比,却是并不一样。
“当时皇上弥留之际,你不能抗旨,我不好违逆,所以才有了此物。只是此物并非遗诏,不得存档便不是明旨诏书,回京之后再做计较吧!若是当时没有海寿在也就罢了,偏生他是亲自盖玺的人……说起这个,宁阳侯家的千金今年及笄,他之前还对我提过,皇上允诺班师之后册他的女儿为丽妃。若是别人不知道也就罢了,倘若知道,恐怕就得耽误了一辈子。”
宁阳侯千金?
张越闻言大讶,心想后世都津津乐道于大明朝后妃选自民间,公主选驸马也都是从民间子弟遴选,却不知道从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