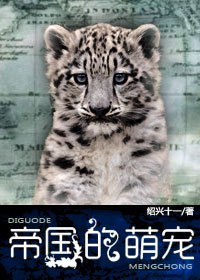冰淇淋王国-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杰里夫·福特
江陵风 译
转自 丁丁虫穴居地
你可记得吹灭生日蜡烛时闻到的那种气味?对于我来说,我闻不到香气,却能听到一种声音,一串拨动小提琴低音琴弦时发出的音符。这些音符和熄灭时的生日蜡烛一样,都蕴含着一个信息:虽然我们又送走了一年的岁月,但同时我们也增长了一年的智慧,那是一种略带忧伤的欢乐。同样,木吉他所弹奏出的音符在我看来就像一阵金色的雨,它们在我眼前从高处落下,直落到心窝深处,然后销声匿迹。我非常喜欢一种进口的瑞士奶酪的原因是:当奶酪在我的手指上如丝绸融化时,我的舌间就尝到了柠檬味酥皮卷浓稠的风味。这些感觉并非是我的想象,它是真真切切存在着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大约每一百万人中就会有九个人具有这种奇特的感觉,这种感觉叫做共感觉,也叫做通感、联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对于我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那就要看怎么想的了。
最近的研究揭示,共感觉的形成区域是大脑里的海马区,一个自古以来就是对感觉进行记忆的部分。外部的各种刺激在大脑各个区域引起的反应在这里得到汇总。据说,每一个人的潜意识中,在一定程度上都曾有过这种不同的感觉交叉重合的体验,但是在人清醒着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混合感觉都被过滤掉了,只剩下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感觉。而对于我们这些少数运气好的人来说,这种过滤作用或者已被破坏,或者太过完美,于是本来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感觉就成了有知觉的意识。也许在相当遥远的远古的某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们都具有这种通感能力,触觉,听觉,嗅觉,味觉以及视觉都可以合为一体,每一个特定事件与我们的感觉记忆结合在一起,伴随着我们的感知能力。我能理解到科学家对通感的解释就是这么多。如今,人们多少都知道点通感的概念。但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当我告诉父母我感到乙烯塑料的低语,紫色发出了恶臭气味,蓝色在旋转,教师的钟也在旋转时,他们却担心我的智商有问题,害怕我的心是一间满是鬼魅的弃屋,充满许多的幻觉。
我是家中的独子,所以我的不正常是这个家庭所无法承受的。何况,我的父母算是老来得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快40了,父亲也已经45岁了 ,在我之前,没能活着生出来的孩子都可以组个足球队了。我5岁那年,只要接触到天鹅绒,就会听到一种声音。我对爸爸妈妈说听到“天使在哭”,从此他们就再也不让我碰天鹅绒了。大人们以为我有病,而且认为总有办法可以治好。为了让我成为一个正常的人,钱对他们而言根本不算什么。因此我小小年纪就得受在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还有医院的候诊室里等候几个小时的折磨,这种折磨持续了好几年。我说不出那些庸医对我的伤害有多深,一大堆所谓的专家教授们,让我做各种乱七八糟的所谓测试,然后对我作出诊断,从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到低智商,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我是一个孩子,十分诚实,如实地讲述了自己感觉到的一切,这正是我一开始就犯下的错误,这个错误导致了以后没完没了的验血、脑部扫描、限制食谱,还要被强迫服下那一大堆可恶的压抑脑部活动的药品,这些药品抑制了我向大人们倾诉那些通感的意愿,但是它们却丝毫不能阻止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我仍然能闻到深秋时节下午金色的斜阳散发出的香草气息。
我的独子地位,加上他们所说的所谓我的“症状”,令我在父母眼中是个不好养的孩子。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少有与其他孩子接触的机会。其原因我想还是得归咎于父母的想法。我与常人不同的感知方式和所说的那些奇怪的的话对于像我父母那样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无法接受生了一个“次品”孩子的事实。他们不让我去学校读书,我的学业是在家里完成的,由父母教我。事实上,我母亲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她是个历史学博士,古典文学的造诣也很深。我的父亲,是一个保险统计师,专门教我数学,只是这门课我显然一直不行,直到进入大学后才有所改观。虽然拿x=y的等式来比喻共感觉现象倒是很恰当,但是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我再补充一点,在我的感觉里,数字8会散发出一种残花败叶的腐臭味。
我所擅长的是音乐。每星期四下午3点,布瑞丝尼克太太会上我们家,给我上钢琴课。她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妇人,却长着美丽至极的纤纤细指,她的手指如此纤细,如此细腻,本应属于花样年华的少女。虽然她的钢琴艺术鉴赏能力不算好,但是她在教导我如何学会欣赏自己的声音方面,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人物。音乐成了我的所爱,当我不被拽出家门四处寻求“摆脱病症折磨”的方法而留在家里的时候,最适合我待的地方就是钢琴前的那条长椅。在我的几乎与世隔绝的世界里,音乐是我逃避现实的一个窗口,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一头钻进去。
当我弹奏钢琴时,我会看到音符在我面前飞舞,就像美丽的烟花一样,五彩缤纷,形态各异。12岁那年,我就开始自己写曲子,我写在纸上的音符伴随着代表不同音符的视觉形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事实上,每当我演奏音乐时,我同时也在作画——在我眼前的空气中作画——真像一幅俄国抽象派画家康定斯基伟大的绘画作品。许多时候,我在一张白纸上构想乐谱的时候,用的是一套64色的蜡笔(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拥有这些画笔了)。比较难用的颜色是绛红色和瓷蓝色,它们给我的感觉和其他颜色不一样,不是视觉,而是一种味觉,因此当我要在乐曲里用这两种颜色对应的音符,我通常会在涂满了五颜六色的纸上写上甘草和木薯来代替它们。如此以来,弹奏的时候就不会出错了。
我在钢琴艺术上表现出来的出色才华却给我带来了惩罚,让我失去了现实世界里唯一的朋友,布瑞丝尼克太太。母亲打发她走时的情景我记得清清楚楚,她平静地点头微笑,知道是为了什么:我已经超越了她的能力,她不能教我了。虽然我知道这事已成定局,当她拥抱着我向我道别时,我还是哭了。当她的脸贴着我的脸时,她对着我的耳朵低声说道,“眼见即为实。”就在那一刻,我知道她已完全理解了我的痛苦处境。我眼见着她沿着小径走去,永远走出了我的生活,她散发出的紫丁香的香味所产生的那种几不可闻的音乐声,双簧管演奏的降B调乐曲,仍然在我的周围萦绕不去。
我相信正是失去了布瑞丝尼克太太才使我产生了逆反情绪。我变得行为散漫,情绪低落。后来有一天,我十三岁生日过后不久,母亲要洗澡,她吩咐我要读完书本上的某一章,但我没有照她说的去做,而是找到了她的钱夹子,拿了5元钱便离开了家。走在蓝天下,沐浴在阳光里,我感到周围的世界充满了生气。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找与我年纪相当的孩子一起玩。我记得镇上有家冰激凌店,以前从医生那里乘车回来时必会经过那里,经常有一群孩子在附近流连。我径直向那里走去,心里直犯嘀咕,担心在我到达那里之前会被母亲抓回去。当我想象着她已经在弄干她的头发时,我拔腿跑了起来。
我到了一排商店前面,其中有一家就是“冰激凌王国”。获得自由的狂喜,和半英里路的疾跑,已让我快喘不过气来了。从正门的玻璃门向里探望,就像在窥视另一个新奇的世界。这里有许多年轻人,还有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他们围坐在许多张桌子前,聊天,嬉笑,吃着冰激凌——不是在晚饭后,而是在大白天。我推开门,闯了进去。就在我进门的一瞬间,这个地方一切神气的魅力似乎都随着我的到来而消失于无形之中了。谈话声停了下来,所有的头都转向我,所有的眼光都盯着我,我在沉默中僵直了身体。
“大家好。”我微笑着招呼,举起手向大家示意,但我的动作已经慢了一步,大家早已转过头去,继续他们的谈话,似乎他们不过是勉为其难地抽出了一丁点时间向门口张望了一下,看是不是风将门吹得一开一合的。我呆立在那里,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我明白要交上朋友还得下一番功夫。
“要些什么?”柜台后面一个高个子的男人问道。
我从恍惚中醒过神来,走上前去准备要些什么。我的面前满是些圆形玻璃杯,上面都印着“冰激凌王国”的字样。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有着如此多的色彩和形体的东西,硬壳果和水果,甜面包和糖块。在我的感官世界里,眼前的景象神奇地变幻成了一种声音,就像是远远传来的汽笛声。整齐摆放的深桶里共有30种不同风味的美食。我的食谱里从没有过任何的糖果或者餐后甜点,餐后能享受到一小点香草冰激凌的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有的医生对我的父母说,吃这些食品会加重我的病症。想到这些,我就要了一大碗咖啡味冰激凌。我之所以选中咖啡味的是因为咖啡也在我的食品禁忌清单上,是另一样我从未有机会尝过的东西。
付了帐,我端着碗,拿了一个勺子,在角落处找了一个座,从那儿我可以看到店子里所有的桌子。我得承认,心里是有些惶惶然,不敢随便找人搭话,因为这么久以来,有那么多大人一直告戒过我不要冒此危险。我的目光在店堂里扫视着,看着其他的孩子们说话,试图捕捉到他们所说的片言只语。终于,我和相隔两张桌子的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四目相对,我笑笑,对他挥挥手。他打量了一下我,然后俯下身去,跟旁边一个孩子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们四个(和他在一起的共有四个人)都把头转向我,看了看我,然后齐声大笑。显然他们是在取笑我,但我却仅仅因为终于引发别人注意到我的存在而沉浸在一阵暖意中。这样想着,我舀起了一大勺冰激凌送入口中。
冰激凌一入口,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通感体验。当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如何描述这种感觉,但是可以这么跟你说:当一个人陷入了混合交叉在一起的各种不同寻常的感官所带来的痛苦,不断挣扎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种“神灵显现”的感觉,一种“我找到了”的满足感。研究超常规现象的人将其名为源自头脑中的“意识流”。一个从威廉?詹姆士处借来的词。第一口咖啡冰激凌给我带来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一种比以往更为深切的“意识上”反应。一个女孩的背影随着这种感觉出现了,她在薄薄的空气中徐徐组合成形,她的出现使得仍然在笑我的那几个人在我的眼中变得朦胧起来。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无论通过哪种感官,味觉、听觉、触觉还是嗅觉,我所能看到的都是些抽象的形态和色彩,仅此而已。但这次和以前都不同。
她稍稍侧过身,猫下身子。她身穿格子花呢的衬衫,外套一袭白色的宽松上衣,头发颜色与我的一样,是茶褐色的,长长的头发用绿色的橡皮圈拢在脑后。突然我看见她将手挥了几下,我这才看清楚她正将一根火柴灭掉,旋涡状的烟雾从她身边慢慢飘散开去。原来,她刚才是点燃一只烟。看上去她似乎是怕被别人发现她在抽烟,当她转过头来警惕地向后看时,我的勺子掉在了桌子上,她的容貌立刻使我着了迷。
冰激凌开始融化,顺着我的喉咙流下,她开始消失。我赶快再舀起一勺,希望再“吃”出眼前的景象来,但是冰激凌还没到我的嘴边,她就突然完全消失了,就像灯被拉灭了一样。这时,我觉得有什么声音轻轻地落在了我的左肩上。我听到了低低的责备声,但完全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知道肩上的是母亲的手,她终于找到了我。我从冰激凌王国走出来的时候,身后是一阵大笑的声浪。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难为情,可当时,即使当我在向妈妈道歉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刚见到的一切。
冰激凌事件后,发生了更严重的事:爸妈在我的壁橱里发现了藏在香烟盒里的药片。这是过去六个月的药片,他们原先还以为我已经吃进肚里去了。这件事使我的父母相信,我的“症状”越来越多,并且正在向着行为不良的方向发展,如果不加制止和管束,在今后几年的时间里我的精神状态将会以几何级数每况愈下。于是他们决定,应该再另找专家来纠正我的行为,父亲又为我找了一个医生,他会使我从一个任性胡言的孩子变成一个听话的孩子。在一次严肃的家庭会议上,我得知了这一点,我除了默认他们的计划还能做什么呢?我知道,在我缺乏想象力的父母想来,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每当我被环境逼得心中激愤难当时,我就开始弹钢琴,有时会连续弹上三四个小时。
斯图灵医生的办公桌位于我们这个镇子的另一头,是一懂破败得几欲坍塌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第一次是由父亲陪我去的,当父亲停在这懂看起来惨兮兮的旧房子门口时,他将地址拿出来至少核对了两遍,以确信我们没有走错地方。医生是个胖墩墩的小个子男人,胡子已花白,戴着一副有着小圆镜片的眼镜,走到门口来迎接我们。我们互相介绍握手时,他为什么笑呢?我一点也不明白,但他看起来是个快乐的人,就像是个Q版的圣诞老人,穿着小了一号的皱巴巴的褐色衣服。他打了个手势,招呼我进屋,但是当父亲也要进去时,医生伸手挡住了他:“请您过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再回到这儿来。”
父亲抗辩了几句,但不起什么作用。他说,他可以帮着一起将我的病史讲清楚。可是这位医生的作法显然不一样,他变得严肃起来,一本正经的,几乎可以说是在下达命令。
“你们付钱给我是给这个孩子治病的,如果您想看病请您去找您自己的医生。”
父亲显然有点不知所措,他看起来还想反对,但是医生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医生跟在我后面进了屋,很快关上了身后的门。
他领着我走过好几间杂乱的屋子,里面排满了书架,其中的一间屋子里,一摞摞的纸堆满了好多张书桌和工作台,他笑着说:“父母双亲就是这样,他们是最重要的,有时候却像沾在鞋子上,甩也甩不掉的东西。除了爱他们,我们还能怎样呢?”
我们走到这懂房子后面的一间屋子停了下来,里面都是一些细细的钢铁搭成的架子,周围镶着格子玻璃窗。阳光倾洒下来,充盈屋内,环绕着我们。架子上垂下了绿色的植物,架子的间隙中也透进来阳光。屋内有张小桌子,上面有个茶壶和两个杯子和几个茶托。我按医生的指示坐了下来,透过玻璃向外望去,我看见他的后院是一个好大好美丽的花园,各种花儿竞相开放,姹紫嫣红,千姿百态。
他给我找了一杯茶,问话便开始了。我虽然在心中努力地抗拒着他,但他的问话方式使我暂时不再想到父亲,这使我开始有点欣赏起他来了。还有,他显然与我以前所遇到过的医生不同,他用一种有所保留的态度和反应来听完我的话,当他问道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时,我告诉他因为我离家出走,去了冰激凌店,他皱起了眉头说道:“这简直太荒谬了。”我不能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