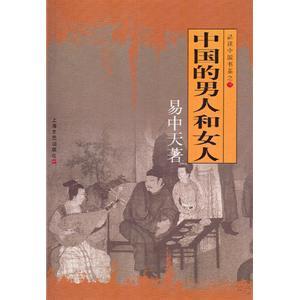爱恋中的女人-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公主做的丝衬衣,红蓝两『色』配在一起很鲜艳,声音木讷地说:“真漂亮——不知谁居然把这两种鲜艳的颜『色』搭配在一起。”
赫米奥恩的仆人悄悄走来。欧秀拉趁机逃走了。她内心十分恐慌,强烈的冲动使她已没有了自制力。
伯基直接走到床前,他心情十分好,身体有点疲倦,跳完舞他感到很高兴。吉拉尔德想跟他聊天,他身着礼服。等伯基躺到床上后,便坐在他的床边,坚持说要聊聊天。
“这两位布兰哥温小姐是什么人?”吉拉尔德问。
“她们住在贝德欧弗。”
“在贝德欧弗。那她们是什么人?”
“中学老师。”
一阵沉默。
“老师!”吉拉尔德终于喊了出来,“我还以为我以前见过她们呢。”
“你失望了?”
“失望?不——不过赫米奥恩怎么请她们来这儿呢?”“她在伦敦认识古德兰——那个黑头发的年轻姑娘——她是个美术家——搞雕塑和制作模型。”
“那她不是中学老师——另一个才是吧?”
“两个都是——古德兰是美术老师,欧秀拉是普通老师。”“她们父亲是干什么的?”
“几所学校的手工艺指导老师。”
“原来是这样。”“阶级障碍很快就会消除的嘛。”
对方带着嘲弄口气的话使吉拉尔德感到不安。
“她们的父亲是几所学校的手工艺指导老师?可这关我什么事!”
伯基笑了。吉拉尔德看到他的脸歪在枕头上,带着一种痛苦冷漠的表情。他更不想走了。
“我想他再也不会经常见到古德兰了。她是一只不安分的小鸟,她这一个星期就要走了。”伯基说。
“她去哪儿?”
“伦敦、巴黎、罗马——天知道。我一直猜测她要跑到远远的大马士革或旧金山去。她是一只极乐鸟,谁知道她到贝德欧弗干什么?事情总是和人们期望的不一样,好象梦一样。”吉拉尔德思索了一阵子。
“你怎么这么了解她?”他问。
“我在伦敦那些怪人中认识了她。”他答道,“她知道米纳特、利比德涅哥夫等人——不过她与他们没有私人往来,她并不是他们那种人——在某方面讲,她更传统化。我认识她有两年了。”“她除了教书还有外快吗?”吉拉尔德问。
“有点,但不经常。她可以卖出一些小模型。她还小有名气吧。”“多少钱一个?”
“有一畿尼的,也有十几畿尼的。”
“那些东西做得如何?都是些什么?”
“我觉得它们有时候做得很精致。在赫米奥恩房间里的那两只铥啕就是她的作品——你见过——是木雕的,而且上了漆。”“我原以为那是件什么粗俗的木雕呢。”
“不,她的可不是,它们就是这样——动物和小鸟,有时候是一些穿普通衣服的奇特的小人像,刻好后的样子很奇妙,它们包含一种无意识,微妙而滑稽的感觉。”
“有一天她会成为著名的美术家吗?”吉拉尔德若有所思地说。“可能,但我认为她不想这样,因为如果有别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她,她就会放弃了美术,她内心里的矛盾是她从事美术的障碍——她不会太认真的,她觉得她可能会献身于美术,其实不然——她一直提醒自己不能陷入太深,这也是我对她这类人不能忍受的地方。顺便问问你,我离开你们后,米纳特怎么样,我没有任何消息。”
“哦,不太是个滋味。哈利戴让人讨厌,在一次该死的争吵中我强压着『性』子才没有扑过去揍他。”
伯基沉默不说话。
“当然,”他说,“朱利叶斯有些不正常,一方面他是个宗教狂,另一方面他又沉『迷』『色』欲。他有时候是上帝纯洁的仆人,给耶稣洗脚的仆人,有时却画亵渎耶稣的画——一正一反,在这两极之间没有别的。他的确不太正常。他需要有一朵纯洁的百合花,正有一位有着波提切利式脸蛋的姑娘,另一方面,他又不能缺少米纳特,让她来玷污自己。”
“这我可不明白了。”吉拉尔德说,“他爱她又不爱她。”“又爱又不爱。她是『妓』女与他通『奸』,地道的『妓』女。而且他很渴望把自己投向她的怀抱,然后他抓起身又呼唤着百合花纯洁的名字,呼唤着那个有娃娃脸的女孩。他就是这样到处享乐。还是那句话——在正直与邪恶之间再没有别的什么。”
“我不知道。”吉拉尔德停了一会儿说。他竟然用这么难听的话来说她。“她给我的印象让人讨厌。”
“但我原以为你喜欢她呢。”伯基说,“我很喜欢她。在个人问题上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事实。”
“我是喜欢她,不过只是那么几天。”吉拉尔德说,“但如果和她呆上一星期我就会反胃。这些女人的皮肤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让你到最后都没法形容那种恶心——尽管刚开始你喜欢这种味道。”“我知道。”伯基说。然后他又很厌烦地加了一句:“去睡吧,吉拉尔德天晓得现在是什么时间了。”
吉拉尔德看了看表,终于从床上站起来,回他的房间去了。但几分钟以后,他身穿衬衣又回来了。
“有件事,”他说着又坐在床上,“我同那帮人吵了一架,就分开了,我还没有来得及给她点什么。”“钱吗?”伯基说,“她可以从哈利戴和其它人那里得到钱的,如果她想要的话。”
“可是,”吉拉尔德说,“我宁愿当时付清我所应付的钱,了结这笔帐。”
“她根本不在乎。”
“是的,也许她不在乎,可总让人觉得把这笔帐结掉要比留着它舒服得多。”
“你这样觉得吗?”他注视着吉拉尔德那衬衣下面搁在床沿上的雪白的腿。这两条大腿,皮肤白皙,肌肉发达,丰满结实,特别漂亮。可这两条腿又使伯基产生爱怜之心,仿佛它们最小的孩子的大腿一样。
“我认为还是结了这笔帐好。”吉拉尔德咕哝地重复说。“怎么做都无所谓。”伯基说。
“你总是说无所谓。”吉拉尔德的神情也好像是拿不主意。他低头凝视着对方的脸。
“都无所谓。”伯基说。
“可她并不卑贱,真的——”
“该是谁的是谁的。”伯基扭过头去。他认为吉拉尔德只是在找话说,“去睡吧,我太累了——太晚了。”他又说。“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什么比较严重?”吉拉尔德眼盯着对方问,等待着他的回答。但伯基把脸转了过去。
“那好,睡觉吧。”吉拉尔德说,亲热地拍了拍伯基的肩膀,然后离开。
第二天早晨醒来,吉拉尔德听到伯基那儿有走动,便叫道,“我还是认为该给米纳特一些钱。”
“哦,上帝!”伯基说,“别太认真了,只要你喜欢,就在你自己心里把这笔帐结了吧,因为你感到似乎良心上过不去。”“你怎么知道我心里觉得愧疚和不安呢?”
“我了解你。”
吉拉尔德思考了一阵子。
“你知道,我认为付给米纳特这类人钱是不会错的。”“对于情『妇』最正确的方法就是看着她们,对妻子最正确的方法就是和她们一起生活。”伯基说。
“没有必要为这件事而恼怒。”吉拉尔德说。
“我觉得挺讨厌的。我对你的过错根本不感兴趣。”“你是否感兴趣,我也不在乎——只是我有兴趣。”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女仆已经来过了,并已经打好了水,拉开了窗帘。伯基坐在床上,懒散而愉快地望着窗外的花园,一片幽绿且无人迹。那种旧式的浪漫的园子。他在想,过去的事物是多么可爱、多么真切、多么具体,噢,这么美的过去,这房子是多么光彩照人又多么宁静。在这平静中已沉睡了几个世纪。然而这美丽的静物又是怎样一个骗局和陷阱。布雷德利是怎样一个可怕的死牢!这里的宁静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禁闭。但是它还是比那些卑鄙的现代人之间的相互诋毁好得多。如果人能按照自己的设想来创造未来——一展生活中的真实与纯真,那该多好,他心里不停地这样喊着。
“我真不明白你到底想让我对什么感兴趣!”楼下的房间里传来吉拉尔德的声音,“既不是米纳特那类人,又不是对煤矿。”“你可以随便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吉拉尔德,只是我自己没法对那些东西感兴趣。”伯基说。
“那么我该做些什么?”吉拉尔德的声音传过来。
“随你便。我又该做什么?”
沉默中伯基知道吉拉尔德在思考这个问题。
“要是我知道就好了。”传来吉拉尔德那和善的回答。“你知道。”伯基说,“你的一部分需要米纳特,只有米纳特,而你的另一部分,又需要矿工和你的生意,只有生意。这样,你已经四分五裂了——”
“我的另外的部分还需要很多别的。”吉拉尔德用奇特的平静而又真挚的声音说。
“那是什么?”伯基感到惊讶。
“那正是我想让你告诉我的。”吉拉尔德说。
又是一阵沉默。
“我无法告诉你。我自己尚且不知我的出路所在,何况你的。你也许可以结婚。”伯基说。
“跟谁——米纳特吗?”吉拉尔德问。
“也许。”伯基说着站起来走向窗户。
“那应该是你的对症良『药』。”吉拉尔德说,“但是你的病已经够重了。为什么你自己不试试呢?”
“我是病了”伯基说,“但我会好起来的。”
“通过婚姻?”
“是的。”伯基固执地答道。
“噢,不,”吉拉尔德马上说,“不、不、不,我的老兄。”他们之间又是一阵沉默,带着一股敌意的紧张。他们之间总是保持着一段距离、一层隔阂。他们俩从来都不想受对方的限制。但又总有一条奇怪的心灵纽带将两人连在一起。
“女『性』的救世主。”吉拉尔德带着嘲讽的口吻说。
“为什么不呢?”伯基说。
“完全不合情理。”吉拉尔德说,“如果那方法有用的话,你将同谁结婚?”
“一个女人。”伯基说。
“很好。”吉拉尔德答道。
伯基和吉拉尔德最后下楼吃早餐。赫米奥恩希望每个人早到。她对她的好岁月快要过去而感到痛苦。她觉得她浪费了生活。她似乎要扼住时间的喉咙,把它们留住。她面『色』苍白而可怖,好象被大家甩在了后面。但她还是有力量,她的意志有种神奇的渗透力。随着两个年轻人的出现,空气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她仰起脸,用她那奇怪的唱歌似的声音说道:
“早上好!昨晚睡得好吗!——我很高兴。”
然后就转过头去,不再理他们。伯基太了解她了。他知道她这样做无非是要显出她不重视他的存在。
“您想要什么,就自个儿从餐柜里拿吧。”亚历山大说道,声音里也轻微地带着些不快,“我希望东西还没凉。噢,不会!鲁伯特,你不介意把保暖炉的火关掉吧?谢谢。”
当赫米奥恩冷淡的时候,亚历山大也改用命令的语气。显然他是从她那里传染的。伯基坐下来,看着桌子。经过多年的交往,他对这房子中的一切太熟悉了,太了解了!这房间、这气氛!但现在他对这一切厌烦透了。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是那样地熟悉赫米奥恩。她直直地坐在那里,沉思着,却显得那么可怕、那么强有力。他对她的了解几近一种疯狂,在这种情况下,让他相信自己没有发疯都是不可能的,也很难相信他不是处在某个埃及法老的陵墓里,是那些死了多年的死尸中的一个。他太了解乔舒亚、马瑟森了。他扯着嗓子迭迭不休地讲个没完,而且话中总是包含很强的知识『性』,总是很有意思。但不管它们多么新颖多么机智,他所讲的都是些司令见惯的事物。主人亚历山大是个现代人,他很随和,不轻易表『露』。马兹小姐只是适当的时候说两句精辟的话。那个娇小的意大利伯爵夫人观察着每一个人,像个在等待时机的黄鼠狼,她只是冷静客观地观察着、从中寻找快乐,而自己却从不参言。布雷德利小姐神态忧郁、恭谨、因为赫米奥总是冷落歧视她,拿她开心,因而大家都看不起她——这是令人感到熟悉的一切,就像已经开局的一盘棋,总是这么几个棋子儿,什么王后、骑士、士兵,和几百年前完全一样,虽然棋子可以变幻着走,但玩法是被大家所熟悉知。总这么下棋,就要让人发疯、累死。
吉拉尔德看样子十分高兴,这种棋法正如他意。古德兰呢,用她那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又『露』出敌对的眼神。她既被吸引,又感厌恶,欧秀拉则脸『露』吃惊,似乎受了伤而不感到疼痛。
然后伯基站起来,走了出去。
“见鬼吧!”他禁不住自语道。
赫米奥恩虽然并不很理解他在想什么,但对他的动作很熟悉,她抬起忧伤的眼睛看着他离去。他的走好象一股浪『潮』,突然而神秘地摧垮了她的身心,只有她那不可战胜的意志没有动摇。她坐在那里思索着,嘴里不知在嘟哝些什么。然而黑暗已经笼罩了她。她好象一艘下沉的船,快要沉没,因为她在黑暗中遇了难。但她那不可战胜的意志机械在支撑着她,让她还保持着那种意志控制着的活动。
“今天早晨我们去游泳,你们说怎么样?”她忽然看着所有的人说道。
“太棒了!”乔舒亚说,“今天天气多好啊!”
“嘿,太妙了。”马兹小姐说。
“好,我们去游泳。”意大利女人说。
“可我没有游泳衣。”吉拉尔德说。
“穿我的吧。”亚历山大说,“我必须去教堂朗诵圣经、他们在等着我。”
“你是基督教徒吧?”意大利伯爵夫人忽然有兴趣地问。“不是,”亚历山大说,“我不是,但我认为应该遵守原有的风俗。”
“这都是些好的风俗。”马兹小姐用优雅的声音说道。“哦,的确是这样。”布雷德利小姐大声说道。
一群人慢悠悠地来到草坪上。这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初夏的上午,这时各种活动开始像人们的记忆一样慢慢展开。教堂的钟声在不远处动听地回『荡』,天空万里无云,异常晴朗。远处的白天鹅像睡莲一样漂浮在水面上,美丽的孔雀欢快地走出树荫来到灿烂的阳光下。
人们也禁不住想沉醉于这完美的境界。
“再见,”亚历山大喊了一声,愉快地挥了挥手套,消失在树丛后到教堂去了。
“现在,”赫米奥恩说,“大家都去游泳吗?”
“我不想去。”欧秀拉说。
“你不想去吗?”赫米奥恩上下打量她一番。
“是的,我不想游泳。”欧秀拉说。
“我也不去。”古德兰说。
“我没有游泳衣,该怎么办?”吉拉尔德问。
“我不知道。”赫米奥恩笑了,声音古怪而开心,“一条围巾可以吗?——一条大围巾?”
“行!”吉拉尔德说。
“那么快点来吧!”赫米奥恩又用唱腔说道。
第一个跑出来的是那个娇小的意大利女人,她好似只猫,两条白白的腿闪闪发亮地向前跑动着。她的头上扎着一块金丝绢,向前伸着。她轻巧地出了院门,穿过草地,到了水边,站在那儿就像一尊用象牙和青铜雕铸的小雕像。她拿下『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