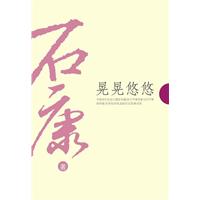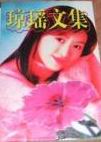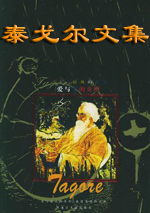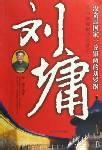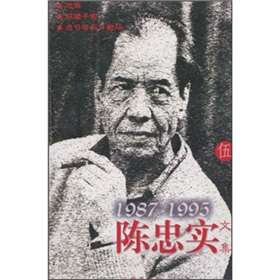池莉文集-第7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三个月后,王劲哉中了古鼎新的计,被日寇生擒,全军随之瓦解,此变震惊江汉平原。王腊狗半年后才知道。
王腊狗为王劲哉叹息了一番,又为自己庆幸。用不着再怕王劲哉,也用不着躲藏了,他对寡妇说了声:“我走了。”掖了枪就离开了沉湖。
13
后来,抗日战争又持续了两年,接着又打了三年的解放战争。在五年的战争岁月里,王腊狗始终像只恋家的狗在沔水镇附近转悠。今儿加入共产党的新四军十五旅,明儿又加入了陈八爹的抗日救国团。因为新四军主力部队北撤,而王腊狗不愿北撤。
日军投降之前,王腊狗不敢回到沔水镇,摸黑进镇过一次,自己家门上一把锁,丁家大门也是一把锁,都躲兵荒去了。
抗战胜利后,王腊狗心想可以回家了。可一进镇就被古鼎新的人认了出来,好一阵追杀。
王腊狗在这个部队那个部队浪来浪去,完全成了个兵痞子。反正他靠一手好枪法打仗吃粮,总之他就是呆在江汉平原上不挪窝。人家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王腊狗倒成了流水的营盘铁打的兵。新四军许多首长知道有一个王腊狗。后来解放军许多首长也知道有个王腊狗。战士们编了一些关于王腊狗的顺口溜。王腊狗听了也不恼。
目录
池莉访谈录
三个女人和男人无数
池莉的小说为什么畅销
池莉的成名
池莉谈高行健获诺贝尔奖
池莉:别再和我谈文学了
池莉的声明:什么是俗?
中年危机——读《来来往往》
写作是一种愉快
像爱情一样没有理由
闲读池莉
小说的标准
珍惜自己
池莉:逃避热闹的女作家
简评池莉
池莉访谈录
新华网(2003…06…25 08:57:56)稿件来源:中国艺术报
文/赵艳
读池莉的作品,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真、实在。她写的都是些琐碎的生活片段,可她一样能把你带进去读,让你感动,感动于生活本身的庸常、平凡、苦恼和淡淡的、然而却持久的温情。她一边注视着生活,一边贴心贴肺地倾诉,一桩桩、一件件直说到你的心坎里去,说出了你的、我的、他的日复一日、细水长流、又爱又恨的日子。谁不是这样活着?谁不是这样辛苦而又执著地活着?平心而论,生命中最实在、最切近于我们每个人的,不就是池莉笔下的那些“日子”吗?也许,和当代的很多作家相比,池莉显得不够深刻,因为她很少在自己的作品中直触灵魂或精神。然而,正如行为是思想的镜子一样,生活的具像也是生活本质的投影。我们不会对表象的生活记载多看一眼,但我们会对从生活中结晶出来的真切的生命片段眷顾流连,哪怕它是世俗的。世俗人生才是生命最本真的一面。也许,生命的本质、日常生活、深刻、诗意等等都应该重新定义,至少,应该有更宽泛的内涵和外延。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池莉的作品虽然没有展示博大精妙的精神世界却依然能够引起我们灵魂的颤动。池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清醒地意识到生活、生活的细节在我们生命中所处的位置,并使自己的创作始终朝向这一方向。她是怎样一路走来的?还会怎样走下去?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走访了池莉。
赵艳(以下称赵):你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开始文学创作了,《妙龄时光》等早期作品流露出青春的诗意,大多具有较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90年代以后,你的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你创作的个性也逐渐成熟。相对于早期作品而言,你认为自己后来的创作的新变和特色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池莉(以下称池):相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潮流而言,中国的当代文学,对于人本身的关注和对于将这种关注高度审美化的思考,都是非常薄弱的。我们长期以来被词藻华丽空洞无物的文章影响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也自然而然地习惯用这种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感情,以及欣赏用这种形式表现感情的作品。新时期以后,思想的解放和文本的尝试才真正活跃起来。中国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实际上也使得世界文学潮流从经济的窗口挤了进来,影响了我们的当代文学。作家们开始有了新的想法,新的念头,新的认识和新的追求,在整个大的走向上加强了对人本身的关怀,对人内心生活的体贴,对于中国人真实生活状态的凝视和思考。我想我就属于这一拨作家。但是,我觉得我更野一些,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盛行先锋探索,其实是摹仿和借鉴,什么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我却渴求对于中国人真实生命状态的描写,并且使用简洁朴实的中国语言,证明这种渴求的作品就是《烦恼人生》了。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总是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直觉,总是觉得摹仿西方的语言和文本,不是那么对劲。探索开始之后,经常冥思苦想。通过这么十几年慢慢地思考,阅读,检讨自己的思想,会见怀有各种思想或者观念的人,与朋友交谈,和他们的思想碰撞,听不同的意见,反复地感觉,其中还包括不断地写作,还包括到处旅行,倾听各种人等的声音,所谓见多识广,慢慢地,我觉得自己的思想逐渐被清理得明晰起来。关键在这里:文学是什么?小说又是什么?人类到底在怎样行进?作为一种文字的艺术创造,一个作家应该怎样去找寻自己敏感的表达方式?于是,我更加明确了:我首先因为自己的生命需要而写作,同时为中国人的生命存在而写作,我敬畏真实的个体生命存在状态,并希望努力为此写出更加动人的作品。
赵:以《烦恼人生》为界,在这前后的变化之外有没有不变的、一以贯之的东西?
池:《烦恼人生》以前的作品只能说是一些习作,作品风格非常不定型,带着青春阶段的生命冲动,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方法,非常容易摹仿。那种幼稚的冲动和敏锐的摹仿,对于真正个性化的文学创作意义不大。但是,在我的作品里头,有一根脊梁是不变的,那就是对于中国人真实生命状态的关注与表达。说得更加具体一点,就是关注与表达中国人的个体生命,这将是我永远不变的情怀与追求。
赵:你在作品中对世俗人生百态进行了仿真写照,但是,在大量充满了生活质感的情节和细节之中,我也看到了许多其他的东西,比如,《锦绣沙滩》、《让梦穿越你的心》的浪漫情怀,《细腰》、《青奴》的诗意化,《凝眸》、《请柳师娘》的感伤情结等等。是否可以说,你虽然致力于世俗生活的表现,但在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追求雅化的作家?
池:在前一个问题里,我已经说到了关注与表达中国人的个体生命状态的问题,实际上对于我追求的东西,对于我具有什么样的气质和特色,都已经不言而喻了。对于中国人而言,何谓雅?何谓俗?难道如古人所说大雅,那些礼仪、道德、伦理以及服饰与诗歌,一直贯穿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吗?像革命期间的白俄贵族在逃亡的路上都带着诗歌朗诵,这种非常雅致的生活是从骨子里保存下来的,中国人显然没有。但是也不能因为没有雅致的生活,就自贬其俗。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俗。俗这个字,在中国语言的意思里,是一个很好的字,人与谷子在一起嘛,只要有了粮食,人就可以挺起腰杆做人了。整个20世纪的世界文学潮流,对于平民阶层,给予了非常的关怀,也就是你们所谓的世俗生活。比如前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就是写世俗生活的作家,再早一年的格拉斯,当然也是。我赞赏他们的这种关怀。只有我们中国很奇怪,自己非常地老百姓,还老是把自己看得高于老百姓。我不想这么虚伪,我本来就是老百姓也乐意为他们写作。要知道,中国老百姓从来都是没有个体生命的,从来都是被强权话语和由这种话语所书写的历史所淹没的,我希望我的写作,关注与张扬了中国人的个体地位和历史。因此,你千万别用“雅化”来分析我的作品和我的内心。
赵:但在你的作品中的确有一股诗意化的情绪之流贯穿其中。如果说,你的作品是一个个日常生活的断片和剖面的连缀或渐次展开,那么,在里面起支撑和依托作用的正是一种诗意,由于这种诗意的存在,作品才浑然一体,充满了内在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池:我的作品当然有诗意,我一点也不否认。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有诗意的。生命的本质就是诗意的。无论他是一个什么人,作为社会的人,无论他的外壳是什么,无论是丑还是美,是贫还是富,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不妨碍诗意的存在。诗意是不局限于任何具体事物的,像罗丹雕塑的老年妓女,你不能说她很丑,也不能说她没有诗意。任何物质碎片,哪怕是垃圾也可以含有诗意。
赵:你所塑造的人物都非常逼真,不管是产业工人、小市民,还是知识分子或者其他人物,简直就是活生生地从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背景中生长出来的,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贴切地吻合于人物的身份。但你作为一个作家,必然有你个人的思想、行为和言说的方式,那么你认为,在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如果有矛盾,你是如何克服的?
池:我这种作家与我写作的人物之间没有矛盾。因为我不是老师,不想当精神导师,不想刻意教诲世人。换句简单的话说:我不推销真理,只是对生活进行审美性的虚构与塑造,我乐意让读者自己从中去获取他需要获得的东西。因此,我自己的言行与思想以及言说方式,与我的小说人物毫不相干。我的人物都是他们自己。从他们的家庭出生,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生长,说处在他们的性格和身份下应该说的话。我对我笔下的人物都是非常重视的,无论短中长篇小说,在我的笔记本里,他们都有完整的出生以及成长经历,都活生生地存在着,我要把他们研究得非常透彻了,有触手可及的把握了,而且我被感动或者打动或者震动了,才会动笔写作。我是写作别人,不是写作自己。我不能让自己来限制我的小说人物。这是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艺术要求。
赵:从1987年的《烦恼人生》开始,你的创作受到了当代文坛的持续关注,不少作品都获了奖。你的小说也很受大众的欢迎,许多作品不但书畅销,而且很快就改编成电视剧、电影,并且受到了国外观众的好评,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池:我当然也很高兴。只是觉得还不满足。因为现在的读者,绝大多数是像你们这样的人群,博士生、研究生、大学生,至少也是高中生。总而言之,都是文化人,而且大多从事文化工作。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作品发行量为几十万册的谈不上畅销,我希望我的读者群能够进一步扩大。因为我的写作对象是大众中真实的个体存在,我希望更多的读者通过对于作品的阅读,认识到自己生活的本质。我希望一个作家能够隐蔽地伴随着许多人的成长,伴随一个人从幼稚、年轻到成熟,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现在我的读者群,许多人就是多年来跟随着我的作品阅读,其心理原因大约也就是这一点吧。
(本文节选自《精神之旅——作家访谈录》,陈骏涛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
三个女人和男人无数
(王玮, 10/20/99 6:41:14 PM)
女人的游戏可不好玩
池莉新作《小姐你早》,乍一看会以为是《来来往往》的续篇,尤其是封面,也许就是在故意为之。当然这都是表面现象,就故事本身而言,还是有着大不同的。
故事中的男人都是配角,主角是三个女人:戚润物、李开玲、艾月,也可以是戚润物这样一个女人。戚的社会角色是国家某部委所属某局一个粮食储备研究所的研究员,同时又是王自力——一个由市政府建委派去做房地产生意而富起来的“王总”的妻子以及一个弱智男孩的母亲。故事开始于1997年春天戚润物因为飞机超员使她的一次出差未成,回到家中却撞上了王自力与小保姆作爱做得“热火朝天”,这一幕让戚润物的人生观或者说世界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加上王自力自作聪明撵走了小保姆换了人生经验丰富感情生活坎坷的老女人李开玲来照顾戚润物——其实是给戚润物找了一个认识现实的导师,在李的影响下,戚润物开始了惩罚王自力的短期和长期行动:先是绝不正中下怀地去满足王离婚的愿望,然后再使他身败名裂,但在他身败名裂之前还要将王的钱财据为己有——所谓“女人的游戏可不是好玩的”以及“女人的顿悟来自心痛时刻”、“别人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身上”、“总有一朵玫瑰停留在夏天的最后”、“最难得的境界还是在人与人之间”如此等等的共10章故事。
女人都那么好
从上述所引那些格言式或者说通俗歌曲式的各章小标题即可看出,这一本《小姐你早》所走的还是通俗小说的路线,其中的人物性格所具备的“典型性”或者说标签化:比如戚润物、李开玲、艾月就被作者强迫着矢志不渝地代表了三个时代以及三种类型的女性(中国的?),也是通俗路线的标准要求,这是和《来来往往》相一致的地方。于是有些叙述就难免理论化了,比如我就很难理解戚润物连卫生巾都不晓得——当然池莉告诉我们了:戚润物从来不看电视,这就好像司汤达要求德雷纳夫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漂亮一样,也好像还珠格格从来不知道有吃饭这回事儿一样——总之戚润物像极了被时光机器送到现在的一个女人,纯洁到了除去研究粮食储备一无所知的地步。我不知道是否武汉这样的科研人员就多,反正我在北京没见过这样的人。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上面使用“理论化”的原因,换言之我是指戚润物、李开玲、艾月其实都是极其理想化的产物,她们具备着女性的美德却全被男人伤透了心。这很正常,在通俗小说中。但《小姐你早》不是一本普通的通俗小说,所以有些麻烦就来了。之所以说其不通俗,我是指这个故事传达的观念不一般,而是很“先锋”,也不能简而言之为女权主义,而仿佛是“天下男人都混蛋”主义,其宗旨便是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