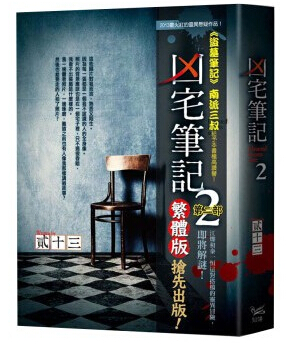情爱笔记-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师,您用不着客气。”年轻的利戈贝托鼓励老人说。“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堂利戈贝托在床上坐起来,被一串有倾向性的笑声所震动。他觉得洗澡间的门随时都会打开,卢克莱西娅太太的身影会像图画一样地出现在门口,她身穿一件那种梦幻式的精致内裤:黑白相间,刺绣制品,有洞眼,丝绸花边,针脚细密光滑,紧紧裹住大腿根,故意突出阴毛,几根小小的阴毛从内裤边缘试探性地——不听话,轻佻地——露出来。那条不可思议地躺在楼梯上的内裤就属于这一类,仿佛是卡塔卢尼人胡安·庞塞或者罗马尼亚人维克多·布劳内尔超现实主义图画中挑逗性的东西;而堂内波姆塞诺·里卡这位好人和天真汉必须从这个楼梯上到自己的宿舍去;在这位老师七年中给他们上过的值得纪念的法律课中,他经常用自己的领带擦黑板。
“利戈贝托,事情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遇到一件麻烦事。虽然我好大一把年纪,可这种事情我一点经验也没有。”
“老师,是什么事情?您说吧!别不好意思。”
为什么不让老师下榻在假日饭店或者希尔顿饭店呢?其他主席研讨会的人不就是住饭店的吗?为什么让他住在国际法女教师的家中呢?一定是出于对他声望的敬重吧。或者是因为他和她多次相遇在法律系?相遇在国际代表大会、讨论会、圆桌会上?或许是合作起草过渊博的论文,里面充满了拉丁语词、大量的注释和令人窒息的书目,发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希宾根或者赫尔辛基的专门杂志上?实际情况是:尊敬的堂内波姆塞话没有去住假日饭店那无人情味的塔楼里,而是在卢克莱西娅老师那舒适、既朴素又现代的小住宅里过夜。利戈贝托非常熟悉那里,因为这学期他和她一起参加了第二学年的国际法研究班;他有好几次登门拜访给她送去作业或者还给她热心借出的大量法规。堂利戈贝托闭上眼睛,他感到毛骨悚然,因为他又一次看到了那位法律女教师离开时优美的形象、苗条的身影和按节奏摇摆的臀部。
“老师,您好吗?”
“好,好,利戈贝托。实际上,是一件蠢事。你会笑话我的。可是我已经说了。我一点经验也没有。我犹疑不决,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小伙子。”
他不需要说下去了;声音在颤抖,仿佛他要沉默,而话语是用产钳夹出来的一样。他一定是在出冷汗。他敢把发生的事情告诉这个小伙子吗?
“你瞧,事情是,从那个会议办的那种招待会上回到家里以后,卢克莱西娅博士在她家里准备了一顿小小的晚餐。只给两个人准备的,对,这也是她的友好表示。一顿非常亲切的晚餐;我俩喝了一小瓶葡萄酒。我是不习惯喝带酒精的饮料的;这么一来,可能我的全部发昏,就是从上脑袋的眩晕开始的。显而易见,是那点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作怪。是的,有些后劲。”
“教授,您就别拐弯抹角了。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
“等一等,等一等。你想想看:吃了晚饭又喝了那瓶葡萄酒以后,那位女博士还坚持我们再喝一杯白兰地。当然,出于礼貌,我不能拒绝。可是,小伙子,那时我头痛得眼睛直冒金星。那是酒精在燃烧。我咳嗽起来,甚至我想:酒精会让我失明的。确切地说,我一定出了什么可笑的事情。孩子,我躺倒就睡着了。对,对,就在那个大沙发上,那个既是客厅又是书房的大沙发上。等我醒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十分钟还是十五分钟?不知道。女博士已经不在房间里了。我心里想,她大概回卧室睡觉去了。我也打算回去睡觉。当我、当我,你想想吧!当我上楼的时候,‘侧’的一家伙,迎面看到……你猜猜什么东西吧?
一条内裤!对,挡住了我的去路。小伙子,你别笑。因为虽说这事再可笑,可我实在是慌乱极了。跟你再说一遍: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堂内波姆塞诺,我当然不会笑的。您不认为那么一条内裤出现在那个地方纯粹是偶然事件吗?”
“什么仍然!什么小事!小伙子。我可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可我也还没有变成老糊涂呢!是那位女博士特意放在那里的,为的是让我看到。那所房子里,除去我和女主人就没有别人了,是她放在那里的。”
“可是,教授,您做为客人,这是遇到最好不过的事情了。你这是受到了东道主发出的邀请了。这再清楚不过了!”
教授的声音中断了三次才说出一句让人明白的话来。
“利戈贝托,你是这么想的?好啦,我也觉得是这么回事。吓了一跳之后,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可能是一种邀请,对不对?不可能是偶然的,整个小住宅都是井井有条的,如同女博士本人一样。内裤放在那里是故意的。再说,放在楼梯上的方式也不是偶然的;我发誓:她在显示它,是故意给人看的。”
“堂内波姆塞诺,如果可以开个玩笑的话,那东西放得可够狡猾的。”
“利戈贝托,其实我心里也在暗暗发笑。也同时又有些慌乱。所以我才需要你出出主意。
我该怎么办?我做梦也没想到会碰上这种情况。“
“教授,您应该做的事情再明白不过了。您不喜欢卢克莱西娅女博士吗?她是个很有扭力的女人;我是这么想的。我的同学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她是弗吉尼亚大学里最漂亮的女教师。”
“这是毫无疑问的。没人怀疑这个。她是个很美的女性。”
“那您就别耽误工夫啦!上去敲门吧!没看见她在等着您吗?一定要在她睡下之前啊!”
“我能这么做吗?无缘无故去敲门?”
“您现在在哪儿呢?”
“还能在哪儿!就在客厅这里,楼梯脚下。要不然我怎么会说话的声音这么小呢。我上去敲门啦?就这么无缘无故的?”
“您一分钟也别浪费了!她已经给您留下暗号了,您可不能装糊涂!尤其是您又喜欢她。
因为您喜欢这位女博士,对不对?教授?“
“我当然喜欢。对,我应该这么做,你说得有道理。可我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谢谢你,小伙子。我用不着特别嘱咐你一定要守口如瓶!对吗?为了我,尤其是为了女博士的名誉。”
“教授,我一定守口如瓶。您别再担心了!上楼吧!捡起那条内裤来!给她送去!敲门吧!先开个玩笑,就说捡到这个吓了一跳。您瞧好吧:结果会美妙无比的。堂内波姆塞诺,您会永远记住这个夜晚的。”
堂利戈贝托在结束谈话挂上听筒之前,听到老教授来不及克制的一阵肠鸣、一阵打嗝儿的声音。他在那弗吉尼亚万物充满勃勃生机的春夜里,置身于那间摆满法律图书的小客厅的黑暗中,该是怎样的紧张和不安啊!因为他要把这次梦寐以求的冒险——在生儿育女的一生中是不是第一次呢?——与掩盖在道德准则、宗教信仰和社会偏见的严肃外衣下的胆怯分离开来。他心灵中搏斗的种种力量哪一种会取胜呢?是欲望?还是恐惧?
堂利戈贝托不知不觉地沉浸在那个已经成为图腾式的情景中了:内裤扔在女教师的楼梯上,他下了床,走进书房,没有点灯。他的身体躲避着障碍物——小板凳、阴沉的雕像、坐垫、电视机——由于坚持不懈的锻炼而动作灵活;因为自从他妻子出走以后没有一夜不是在失眠的推动下起床摸黑,去书房的故纸和图画里寻找消愁和解闷的安慰。脑袋仍然专注于被那个情节(化做一条芳香、淫荡的女人内裤,摆在楼梯的台阶之间)淡化的可尊敬的法学家的身影上,很像汉姆雷特式的犹豫踌躇,但是堂利戈贝托已经坐在书房的长木桌前翻阅笔记本了;当电灯的金色光芒照耀到那一页开头上的一句德国谚语时(谁有选择,就有烦恼。),他震惊了:非同寻常!您不知道从哪里抄来的这么一句谚语,不是正好描绘了那可怜又幸运的堂内波姆塞话的精神状态吗?老先生已经被充满魅力的女教师卢克莱西娅给迷住了。
他的双手本来是在随手翻阅另外一本笔记,想着一看是否能第二次在为他的想象力提供燃料的梦境和现实之间确立一种关系,这对突然停了下来(“仿佛赌场收付员朝旋转的轮盘赌上抛球的手一样”),立刻如饥似渴地埋头写起来。关于帕特丽夏·希戈斯米特的(伊迪斯的日记)的一些思考,胡乱地写在那一页纸上。
他抬起头来,感到困惑。他听到从悬崖下传来的大海愤怒的涛声。帕特丽夏·希戈斯米特?那个写令人厌倦的犯罪小说的女作家,他一点也不感兴趣,因为总是由那个冷漠而无缘无故的罪犯里普利干的坏事。过去他一向用打呵欠的方式来回答那几年里由这位女作家在利马成千上万的读者中(通过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掀起的时髦(可与《生着和死着的西藏》相比)。这个随着电影风向写作的二流作家钻到他笔记本里来做什么?他甚至连什么时间和为什么要写下那篇关于(伊迪斯的日记)的评论都记不清了,甚至连这本书也给忘了。
评论是这样写的:“优秀小说,可以了解虚构是一种想象世界中的神游,可以弥补生活的不足。伊迪斯家庭、政治和个人的失意不是凭空而来的,其根源在于那个让她更痛苦的现实:她的儿子克利菲耶。他不是像在(日记)中那样设计的——一个懒散、屡屡失败的青年,大学没有考上,又不会工作——在他母亲写的字里行间,他脱离了原稿,出现了伊迪斯希望他过的生活:当上一流记者,与一个家境良好的姑娘结了婚,生儿育女,有个好职务,让他母亲感到非常满意。
“但是,虚构是个暂时的办法,因为它虽然给伊迪斯以安慰并且让她不注意受挫折的一面,却限制了她为生活而进行的斗争,把她孤立在一个内心世界里。她与朋友们的关系淡薄了,受到了破坏;丢了工作,最后落得无依无靠。尽管她的死有些夸张,从象征的角度说,是有联系的;从肉体的角度说,伊迪斯过渡到了生前已经变化的世界中去了:非现实性。
“这部小说是用骗人的简单方式营造起来的,在这个方式下面展现出一个戏剧性结构,展现了敌对的姐妹之间、现实和欲望之间的殊死斗争以及它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有人类精神的神奇领域除外。”
堂利戈贝托感到牙齿在打颤,双手在出汗。现在他回忆起来那部转瞬即逝的小说和思考它的原因来。他会像伊迪斯那样由于滥用想象力而滑向毁灭吗?但虽然有这件事,有这个与死亡有关的假设,那条内裤、芳香的玫瑰,仍然留在他意识中。堂内波姆塞诺那里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与年轻的利戈贝托通过电话之后,他的动作是什么?他的选择是什么?他是不是接受那个学生的劝告了?
他已经开始跟着脚尖上楼了,周围半明半暗,可以辨认出放图书的搁板和家具的轮廓。
他在第二级台阶上停步,弯下腰去,用僵硬的手指抓住那件宝贝——是绸缎的?是针织的?
——他拿到鼻子下闻了闻,仿佛一头小野兽在察看这个陌生的东西是不是能吃的食物。他半睁半闭着眼睛,吻了一下内裤。开始感到一阵让他发抖的眩晕,便赶忙抓住了扶手。他下了决心,要干下去。他继续爬楼梯,手里拿着那条内裤,一直跟着脚尖,担心被人发现,或者是害怕响动——楼梯轻微的吱吱声——会破坏了这个美梦。他心跳得特别厉害,因此闪过此事不宜的念头,除了愚蠢,有可能在这美妙的时刻由于心脏病发作而躺倒。没有,不是晕厥,而是好奇心和品尝禁果的感觉(一辈子都没有过)在加快血液循环。他终于到达走廊尽头,站到了女法学教师的住房门前。他用双手紧紧地托住了下巴,因为牙齿打颤的荒唐样子会让女主人产生极坏的印象。他鼓起勇气(堂利戈贝托大汗淋漓的同时又在发抖,他低声说:“他是强打精神!”用指关节敲敲门,动作极缓慢。房门没有上锁,好客地吱扭一声就打开了。
这位法律系哲学教授站在门里地毯上看到的景象,改变了他对世界、人类——肯定还有法律——的观念;这让堂利戈贝托狂喜地发出一声叹息。从弗吉尼亚州满天星斗的空中,一轮金黄的圆月发射出的带靛蓝的金色光芒(是梵高的?波提切利的?某个表现派画家比如埃米尔·诺尔迪的?),在一位要求严格的舞台设计师或者熟练的灯光照明专家的安排下,整个落在床上,唯一的企图就是突出女教师的裸体。谁能想象得到她那在讲台上展示的楚楚衣冠,那在代表大会上陈述论据和提案时穿戴的剪裁入时的服装,那在冬天时常裹在身上的风雨衣,竟然掩盖着普拉克西特利斯为着和谐、雷诺阿为着肉感的塑造而争论的形体呢?她脸朝下躺着,头部枕在交叉的双臂上,因此这个姿势加长了她的身材,但不是肩膀,也不是柔软(“是意大利语意义上的‘柔软’。堂利戈贝托如此确定道,他对任何阴森的东西没有丝毫的兴趣,反之都很喜欢”柔软“)的胳膊,也不是脊背的曲线;这些都没有吸引住堂内波姆塞话的视线。
也不是那乳白色丰满的大腿和那双玫瑰色的脚丫子。而是那两个快乐得厚颜无耻地翘起和炫耀的肥臀,仿佛双峰山的圆顶(堂利戈贝托高兴地联想道:如同日本明治时期版画中白云缭绕的群山峰顶。)可是还有鲁本斯、迪西阿诺、库尔贝、安格尔、乌尔古罗以及六七位创作女性臀部的大师似乎搭帮结伙地要表现那昏暗中发出白色磷光的肥臀,要显示它的坚实、牢固、丰满,同时还有精致、温柔、灵性和令人产生快感的颤动。堂内波姆塞诺这时已经眼花缭乱,无法控制自己,(难道永远堕落了?)不知不觉地向前迈了两步,走到床边跪了下来。多年的地板发出了抱怨的声音。
“女博士,清原谅,我在楼梯上捡到了您的东西。”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同时觉得一串串口水从嘴角里流出来。
他说话的声音太低,连他自己都听不清楚;或者也许是仅仅抖动了嘴唇而没有发出声音来。可无论是他的声音还是他的出现都没有能够唤醒女法学教师。她呼吸平静而均匀,处于天真无邪的睡梦中。但是,这样的姿势:裸体,紧挨着卧室的房门,披散着头发——浓密、乌黑的长发——垂落在肩膀和脊背上,与皮肤的白皙形成强烈反差,能是天真无邪的吗?堂利戈贝托的判断是:不可能,不可能。那位备受折磨的教授也随声附和地说:“不可能,不可能。”他的目光在那波浪起伏的体表上移动着,在她身体的两侧,女性的肌肉在月光下显得高贵起来(堂利戈贝托纠正道:确切地说是被迪西阿诺笔下昏暗中一个个肉体的油光给衬托得高贵了。“)仿佛汹涌的大海一样就摆在他目瞪口呆的面前:”这不是天真无邪,绝对不是。我来到这里是因为她要我来的,是她策划的。“
可是,他不能从这个理论化的结论中吸取足够的力量去做一再出现的本能强烈要求他去做的事情:用手指肚去抚摸那缎子般光洁的皮肤;用夫妻亲吻的嘴唇放在那山峰和洼地里,那里温暖而芳香,散发着甜味和咸味共处但不混杂的一种气味来。可他没有决定做任何事情,因为幸福得愣住了,只是一味地看个不停。这个奇迹从头到脚上下来回多次以后,一次又一次传遍了全身,他的眼睛静止不动了,仿佛无需再继续品尝的鉴赏家一样,因为他已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