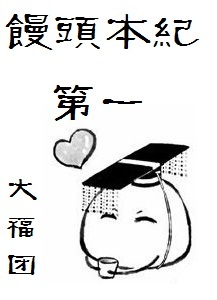权臣本纪-第14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眼见天渐渐黑去,成去非便吩咐人布置饭菜,一旁吴冷西则道:“老师现如今习于一日两餐,已用过饭。”成去非垂了垂眸,低声道:“学生同老师自嘉平三十年一别至今,老师的习惯变了,学生也无从得知。”水镜除却当年于会稽收他三人教授课业,再也未纳入门弟子,待成去非十六岁重回乌衣巷,便云游四方讲学,居无定所,是故一别几载,并不算出奇。
“老师这回既好不易来了,且住一段时日,学生自当为您请良诊治腿疾。”他不无关切,吴冷西连忙也在一侧附和了两句,三人中倘能有能留住老师的,也独成去非了,不过老师性情亦是拘束不得,话虽如此,留不留,还是要看老师意愿,水镜已轻声道:“这两日子炽将你的事情一一说与我听了,文治武功皆大善,我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言外之意十分清楚,成去非默了默,接道:“家父业已不在,学生最挂心者莫过于老师,学生也希望老师能留在建康。”
“伯渊,”水镜唤了他一声,“我亦衰朽,终有一日要离你们而去,许是明日,许是明年,”他枯枝一样的手忽抬起在成去非头上轻拍两下,叹息道,“你的路,早就衙的,要一个人走,伯渊,可是觉得孤独了?”
老人苍然的声音猛得直撞心底最柔软处,成去非抬眼望着恩师,没由来的心酸,即便是面对父亲,他也未曾有过这般心境,良久,方答道:“学生痴愚一念,至死不改,无怨于人,无怨于天。”吴冷西听得心头一凛,不由呆呆看着他,亦知他那颗心到底未变,一时更是无言。
“人这一生,有一件九死其尤未悔之事,不忘本心,穷且益坚,可托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便是真君子大丈夫了。”水镜语调缓慢,鼻翼嘴角皆是沧桑老态,纹路纵横,微微下垂的嘴角更显疲惫之色,看向成去非的目光却复杂难言,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唯独他倾尽毕生心血所栽培起的第一得意门生,却注定要孤独背生向死,死后方生,这是他的不幸,还是他的不幸?亦或是两人的大幸?
灯枯油尽的老者,在久久凝视着爱徒的一刹,心底已辨不清是欣慰还是酸楚,眼前人从年少时便选定一条世间最难走的路,世间路千万条,他本不必如此,但这条路,终究有人要走,无论百年,千年,这人世终将有那么一人,来走此路,那么他的丹心,也必将照着汗青……水镜双眼渐渐浑浊,低下头来,不无伤感喃喃道:“伯渊,老师知你孤独,知你孤独……”温润谦和的老者,半生归来,仍身无长物,孑然一身,只是将另一样孤独传至眼前人脑中心底,薪火不灭,高洁清白。
成去非深深缄默,他的老师确是老了,否则便不会有如此怅然情态,或许人老了,便是这般心肠?但无论老与不老的恩师,即便只是端坐无声在此,也自有熨帖心灵之功效,他的眼前身后有师者在,大约就可抵寒宵冷雨,道不孤矣。
“师哥,”吴冷西见状便有心打破这突如其来的沉寂,“老师昨日尚提及多年不见你书写,我去为师哥研墨抻纸罢?”说着窸窸窣窣起身,水镜已瞧见墙上所挂一行字,却因眼花厉害,并不太能看得清,遂问道:“伯渊,那墙上所书为何?”成去非一面挽袖,一面答道:“落日胡尘未断。”水镜沉吟良久,方道:“新律既定,让你师哥去西北,唯教化可真正收纳人心,西北向来不重于此,伯渊,你以为呢?”成去非在案头落笔应道:“老师说的这事,学生亦早有想法,只是边关苦寒,师哥的身子不算康健,我正担忧此点。”
“这件事,总要有个开始,去并州吧,刺史府里也好协助。”水镜叹道,“此事要经几代之功方可见功效,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去非拈起写好的大字朝榻边走来,跪倒道:“老师目光之远,学生不能及,”说着将那字凑近执与水镜看,笑问:“老师看学生的字可有长劲?”
师生离得极近,仿佛又回到十几载前会稽授业时光,水镜含笑认真看了两遍,点头道:“骨力见长,甚好,甚好。”吴冷西净了手也回到这边来,笑道:“师哥的字在江左虽独树一帜,只是老师不知,师哥家中有人可将他的字学有十二分像,了不得。”
吴冷西无意一说,忽觉失言,不禁望了望成去非,成去非却并不以为意,继而解释道:“是我一位娘子。”吴冷西面上一红,知道自己确是失言,遂尴尬笑道:“我倒有些饿了,先去寻些点心吃。”成去非笑着点了点头,随他去了,待他离开,忽正色道:“既说到我这位娘子,学生有一事想告诉老师,我这娘子来历有些曲折,是阮正通家中所收养孤女,因缘际会得以来我家中,因她性情温柔,学生便留了她,我也得以知道些阮家秘事,老师,”他压了压声音,“宗皇帝当年的遗旨,正是大将军,并非先帝,那道圣旨就在学生这里。”
水镜点点头,似是并不意外,成去非未免有些不解,却听水镜已道:“既如此,伯渊,你有何用处呢?”成去非心头跳了几跳,看看恩师,轻声道:“老师最了解学生,学生无所隐瞒。”水镜闻言缓缓摇首:“我进来时,仔细打量你,想到的正是‘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一句,不到万不得已,我本不希望你如此,只是日后之事,无人能料,你可知我祖上是何人?”成去非一愣,道:“学生不曾听老师谈过一己私事。”
“我祖父,正是前朝最后的废太子。”
老师的语气平淡至极,成去非一时错愕,无话可接,水镜面上并无关于旧事的太多情绪,唯有喟叹:“荆棘铜驼之悲,不过输赢皆化焦土,干戈之下,最苦莫过于黎庶,你要慎之。”
这态度并不明朗,成去非默然,许久方道:“学生谢老师教诲。”
待星辰漫天,夜色深重,师生叙话已久,水镜先生仍要回吴冷西那里去,成去非知留不得,遂还将老师背出,握住那干枯泛凉的手时,到底是不舍,遂低声求道:“老师,还是多留几日吧,学生下朝后去师哥那里看您。”水镜拍拍他手掌,终点头应许:“伯渊,我知道了,我会留下几日。”不过成去非这边还是放心不下,命赵器一路相送,自己则躬身施礼直到听不见那渐行渐远的铃铛声才直起腰身。
迈上台阶时,不知怎的,又情不自禁回首看了一眼,黑魆魆的一片,真的什么也望不见了,亦听不到了,想老师那佝偻身影,毕竟没忍住,引袖拭了拭眼角方踏入家门。
第230章
京中的天气已渐热; 不免容易困乏。不过但凡有任何风吹草动,消息照例传得飞快。水镜先生本次自山东讲学归来,顺道至建康,并非大事; 水镜其人名声在会稽更盛; 建康未必入眼,但先生第一门生正是名动天下的乌衣巷大公子,时人不得不高看此人。成去非的少年时代本就是一团迷雾,昔年沈氏同成氏离婚一事虽也满城风雨,轰动一时,但时过境迁,也渐渐复归平寂,直到成去非十六岁回京都; 起家官便是台阁尚书; 接手实务,而非清要之职,已十分瞩目; 再到钟山事变一出; 时人惊叹太傅有子如此的同时,自然对其之前十几载的会稽光阴有暗窥之情。世人皆知乌衣巷大公子受业于山中高士; 但真正见过水镜其人者寥寥,或传言其人严苛寡情; 或传言其人诸子百家、天文地理、农事兵略、五行八卦、奇门遁甲、无一不通; 是故才有大公子今日之性情; 今日之才学。
但知情者一如御史中丞沈复,清楚乌衣巷成去非实乃多得其母性情,容貌气度、行事手段无一不类沈氏,月明林下的美人,绝非只有女子的柔弱屈从,而自有独立孤园的神勇,是以她一往无前,一去不回的姿态,至她唯一的子嗣这里,经骨血相传,化为更为决绝乃至看上去也更为无情无欲尖刀淬火的一张面孔。
而真正的水镜先生,依凡人所见,不过一寻常老翁,即便顺时光之河溯回而上,那十几载前的水镜先生,也仍是那般模样:芒屩布衣,安之若素,极为冷酷,又极其温柔。
千里古道,万丈西风,皆在先生一双麻履之下。
大司徒府在清谈正酣时,亦无可免俗谈及水镜,至于偌大建康,谁人第一个得知水镜先生的到来,无处可考,也无关紧要。待在场诸人问及水镜出身,竟是有百样说法,口径难能统一,众人定夺不下,遂笑问大司徒,虞仲素也只是抚须道:
“寒门英俊,诸位又见过几人呢?”诸人一笑,有人接道:“是了,怎会是小门效出身,只是不知这水镜先生到底是何来头?”旁人纷纷附和相问,大司徒笑道:“伏虎卧龙,又何须出处?”在座这些人又是一愣,更加摸不清这话里头意思了,一人坐的离顾曙近,不由倾身问道:“仆射向来最懂大司徒,大司徒这是何意?”顾曙却笑言:“将那水镜先生请来问一问,诸位便知道了。”这人略略一想,看着顾曙认真道:“未尝不可,仆射可与之辩《易》。”顾曙遮袖仰首饮了酒,笑而不语摇了摇头,这人便望向大司徒道:
“水镜先生亦算天下名士,倘能邀来谈玄,倒是美事。”一时众人就此说笑半日,忽听远处闷雷滚过,骤风顿起,吹得凉亭四下薄幕飞卷不定,烛火摇曳欲灭,看样子大雨将至,便纷纷起身告辞,管事忙去给备雨具,不多时,诸人散尽,眼前所剩的一片残山剩水也被拾掇干净,只留几样蔬果。唯顾曙未走,闪电乱窜,闷雷渐近,他便起身在亭柱旁观望天象,不禁想起一件旧事:
嘉平二十九年,也是初夏,一众四姓子弟于亭中切磋书法,成去非难得肯出手,倚柱书写,天象忽变,霹雳破柱,成去非衣裳焦然,左右子弟皆跌宕不得住,独他神色不变,书写如故,遂得“雅量”之名。
可这世上,难道就无可让乌衣巷大公子怫然变色的事情了么?顾曙微微一笑,仿佛那云层波涛明灭间潜着一条无形巨龙,他想了想方才虞仲素的那两句话,于是回首笑道:
“静斋的听涛小筑此刻当别有风味。”
雨倾盆而下,虞仲素叹道:“何时静斋能如阿灰这般儿女双全,他便是日日不出听涛小筑,我也随他去。”顾曙道:“世伯勿要忧心,静斋哪一日忽回心转意,也极有可能,人,并非一成不变,只是台阁怕很快又有事需静斋操劳。”虞仲素听他别有意味,遂笑道:“尔等台阁后生,哪一个不辛劳?”顾曙信步走回,复又坐下,随意拈起一颗新湃的樱桃,只是把玩:“世伯不知,大公子有意并官省职,精简机构,此一事,提过数次了,倘真是行起来,自然是静斋这个大尚书最为辛苦。”虞仲素颇为意外,面上却淡,沉吟道:“伯渊提将此事了?”顾曙笑着点点头,虞仲素阖目听了片刻风雨声方道:“他这老师果真教的好。”
“水镜先生能得大公子如此高徒,此生无憾,未必就比不上帝师。”顾曙的失言处如水无波,似是毫不在意。虞仲素亦当秋风射耳,不与点评,只问道:“阿灰家中有水镜的诗文集?”顾曙笑道:“不过是内子嫁来时所带,世伯知道,水镜先生在会稽闻名遐迩,偶有诗文流出,自然是洛阳纸贵。”虞仲素道:“阿灰看那手笔如何?”顾曙的神情倒像真的仔细回想了番,答道:“说也奇怪,这水镜先生的诗文乍读极为冲淡,犹之惠风,荏苒在衣,但有些断句却又隽永深沉,似别有所指。”
别有所指的自然是阿灰,虞仲素不过在心底骂了两句竖子狡猾,便道:“阿灰说来听听。”顾曙索性卖关到底:“晚辈回头将那送来,世伯不妨亲自看看,晚辈只是觉得这世上,那些自诩许由巢父的人物,未必就真肯听鹤群中,布衣巷里,不过掩人耳目罢了。”
话中越发有话,虞仲素沉沉一笑:“阿灰这话不留情面,不像你平日。”顾曙则笑道:“就是菩萨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晚辈不过有感而发,让世伯见笑。”
“文为心声,人如其字,阿灰可能猜出水镜先生到底何人?”虞仲素冷不妨问道,顾曙淡淡一笑:“方才世伯不是说了么?伏虎卧龙,大公子的老师,怎会是常人?我听闻大公子十分敬重此人,曾与人云老师乃亚父,毕竟此人长伴大公子数十载。大公子今日之铸造,不是水镜之功?亦或者,大公子天生一脉奇骨。”末了的话则更像无心调笑,顾曙说的轻松自在,这方将樱桃送入口中,顺道赞了两句,忽想起什么,面上笑意更重,“难怪大公子放不下史青,人总是物以类聚的。”既说到史青,心底随即动了动,史青终如愿得大司农之位,不知是否时时会想起皇甫谧,他的老师,可是死在这个位子上的。而史青如今反夺度支部诸多事务,顾曙早有觉察,想到此,嘴角那抹笑意便寒了几分。
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变化莫测,犹如人心,远处天角已露几颗星子,顾曙整整衣裳起身施礼笑道:“属官们怕是路上得淋雨,晚辈倒得了个便宜,夜色已深,不敢再叨扰世伯,明日我便命人将那诗文集送来。”
是以虞仲素也不强留,命人挑灯相送。这边顾曙回到府里,把水镜那本《东堂诗文钞》寻出,扫将题目时不由冷笑一声,随后正欲唤而,而却先行来了,一脸苦笑:“公子可回来了!”说着把加急的书函呈了过来,顾曙甩开细看,心中先是一沉,继而面庞浮上丝缕笑意,举手顺势烧了,吩咐道:“研墨,我这就回信。”
等提笔时边写边道:“明日将这本《东堂诗文钞》送去大司徒府上。”而敛手于一侧瞧了两眼,奇道:“这是今上所写?”顾曙虽忍不住失笑,心中却十分满意,道:“你不是见了东堂二字,就当天子上朝也要写诗作赋?今上不爱动笔墨的,也无此雅兴,可惜了那一手漂亮行书。”而面上尴尬,顾曙又笑道:“即便真是今上所书,我岂敢将天恩送人?你倒是糊涂了。”而唯唯笑应:“公子说的是,小人不过一时无脑,脱口而出。”顾曙却接道:“无脑?无脑有无脑的佳处,世生一切,皆有用也。”
这彻底将而说得懵然,一时却也无话,无意间终瞧见“水镜”二字,方恍然悟道:“原是水镜先生的大作。”顾曙跌足笑道:“怎么,你也拜读过?”而道:“小人自然没有,不过这人既是皇族后裔,又是大公子老师,写的东西自然是好的。”
水镜先生的来历,而早遵顾曙吩咐于暗中查明,当初得知时,顾曙方也了然,这便不出奇了,前朝废太子生前便喜交文人雅客,编纂文集,身边有号称“东朝十友”的才子能士,即便世道全变,水镜到底是这大树延伸出的枝叶,根基雄厚,养分充足,后人亦得滋养。水镜一身才学,大可解释得合情合理。
“写得确是妙。”顾曙且又随意一翻,恰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两句入目,他无声笑看有时,轻轻合上,里面诸如此类文句俯拾皆是,他不担忧大司徒那颗刁钻机巧心只会欣赏锦绣佳句,而大司徒今晚言辞,顾曙则不免多有联想,水镜的身份,大司徒极有可能亦是一清二楚,那么将文集送去,大司徒亦要作如是想法看待自己,于他,无谓无妨。如此想了半日,顾曙将书函封好,仔细交待一番,方命而去了。
之后几日间又连着下了几场暴雨,江南已进梅雨季。水镜先生因这雨天,腿疾更重,成去非每日公务忙完,必要亲临侍候。这日正要撑伞自台阁出,内侍黄裳却忽然造访台阁,云今上要看西南益州来的折子,折子正是石启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