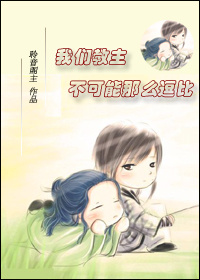长公主不想死-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寒暄了一会儿,张太后才终于切入了正题,“有一件事,我存在心里不知能与谁说。思来想去,也只有来问真师讨个主意了。你一向待我们母子亲厚,切莫推辞,将来陛下长大了,也必然记得真师的恩情。”
这话就说得重了,贺卿虽然知道不会是什么简单的事,但话说到这里也无法推辞,只能硬着头皮道,“我能力有限,却也愿意尽心竭力,太后娘娘但说无妨。”
生产之后,邱姑姑就回到了太皇太后那边,张太后本人有了底气,坤华宫里用着的便都是自己提拔上来的。即便如此,她也屏退了众人,这才压低声音问,“听闻正是真师向太皇太后提议,为吾等查验孕事,可有此事?”
“是。不过也是太皇太后明察秋毫,太后娘娘福泽深厚的缘故。我不过白说一句话罢了。”贺卿道。
张太后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抬起头来逼视着贺卿,“哀家还听说,在那之前,朝中已经推举出了数位可以承继大统的藩王,想来也不会有假?”
贺卿眼皮一跳,终于知道张太后如此大费周章,是为什么了。
藩王入京,自然也包括了那几位被推举过的。
他们自己是否知情?他们身后是否还有推手?如今新皇已经诞生,登基大典在即,这些人可曾死心?藩王入京朝贺,是否存了别的心思?
这些问题,别人可以不想,张太后却不能不想。
作者有话要说: 看到捉虫的才发现女主名字写错好几次……都是隔壁的女主角,还没扭过来【擦汗
第31章 政治斗争
“太后娘娘从何处听来这个消息?”想明白了此间因果,贺卿并未立刻回答张太后的问题,而是反问道。
张太后略一迟疑,方道,“是下头的人禀报……”
“此事隐秘,当时不曾传出消息,如今自然更不会。”贺卿面色严肃,按住张太后的手,“如今大局已定,追究这些事也毫无意义。太后娘娘切莫被有心人挑拨,失了平常心,乃至与太皇太后生出嫌隙。”
“真师所言不差,只是哀家心里着实放不下。”张太后轻轻叹了一口气,“陛下年幼……”
“太后娘娘想差了。”贺卿打断她的话,“当日陛下尚在母腹之中,连是男是女都不知晓,太皇太后和满朝重臣却还是选了他,为何?”
“他是先帝子嗣。”张太后说着,自己也醒悟过来,低头道,“是哀家想差了。”
如今的局势,无论如何不会比当初更差。既然那时能坚持,如今又岂会轻易更改主意?她若是被这些流言乱了心思,内乱一生,反倒很有可能会给太皇太后和朝臣们带去麻烦。
想到这里,张太后不由一阵后怕,拉着贺卿道,“多亏真师提点。”
她是母以子贵,才得以坐上太后的位置,享受这般尊荣,所以对这些事便会格外在意,偏偏又对朝中局势不甚明了,才会被人轻易挑动。但此刻被贺卿三两句话一说,思路便立刻清晰了。
只要记得太皇太后和朝中那些相公们都会奉她的儿子为帝,不论遇到什么事都有他们挡着,自然就不会轻易被动摇。
所以那个问题,张太后没有再问。
不知道也好,知道了不免心有挂碍,说不得反而会叫有心人看出端倪。张太后不算太聪明,但在这深宫之中,她也有自己的生存智慧。
这个话题就此略过,张太后叫人抱了小皇帝过来,逗了一会儿。
这孩子已经四个月,皮肤完全长开了,十分健康好动。虽然还不会爬,但只要把他放在榻上,他就用四肢和头着地,几处用力,在榻上挪动,乐此不疲,叫人看了十分好笑。
一个懵懂的小生命,总是让人心情愉快的。
但从坤华宫中出来,贺卿脸上的笑意便很快散去,变成了严肃。
张太后能听到这种挑拨,可见某些人的确存了别样的心思。而且,他们的势力可以渗透到宫中来,恐怕绝不会小,不知会将多少人都卷进去。
眼前春光明媚,草长莺飞,贺卿却莫名看出了一点风雨欲来的压抑。
不过,这已经与她没有关系了。这样的事,想来太皇太后和朝臣们不会毫无准备,如今她已经从中抽身,也不必再搅和进去,倒也乐得安心。
有那功夫,倒不如多想想报纸的事。
古籍之中关于这方面内容的记载实在寥寥无几,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能用的都已经用尽,声势也已经足够,也是时候减少无意义的彼此攻讦,引导这些读书人主动去探寻真理,发前人所未见了。
就算真的要争个胜负,也别在口舌上,得拿出真本事来。
想到自己的事业,贺卿立刻振作起了精神。等她回到问道宫时,已经将宫中那些乌七八糟的事都抛在脑后,愉快地换衣服出宫去了。
意外的是,在报社,她竟然又见到了顾铮。
如今朝中正是最繁忙的时候,要为下个月的登基大典做准备,顾铮这样的重臣,自然是无暇分身的。贺卿也已经许久未曾见过他了,所以骤然在此处见着人,不免有些惊异。
不过,对于顾铮到这边来,她还是十分欢迎的,“顾大人真是稀客,今日怎么有空过来?”
“办事时正好路过此处,就进来看看。”顾铮道,“这几个月,报纸上可是热闹得很。只是我看他们都快词穷了,这么吵下去毫无意义,恐怕真师也要变一变了吧?”
他说着扬了扬手中的样刊,“这下一期的主题,倒是有些意思。”
贺卿最终选择了力学作为切入点,不但因为它是整个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也是现实生活中最常见、运用最多的部分,更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它不犯忌讳。
像天体物理这种内容,贺卿至今从未提起过一言半语,日心说也同样没有涉及,只因在这个时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涉及到占卜的内容,乃是“天启”,是朝廷明令禁止私人学习的,只有担负相关职责的官员,才可以世代沿袭。
当然,若说民间绝对没人偷偷学,那必然也是假话,否则古往今来就不会有那么多山野高人出现了。
但没有人会对外宣扬,更无法想象将之发展成一个学科。
所以贺卿思来想去,还是选择了从基础入手,慢慢来。
此刻见顾铮提起,便笑道,“这头版的文章本该请顾大人主笔来写,只是如今朝中事务繁忙,不敢搅扰。如今这一篇,我却是不怎么满意,只是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正为此发愁呢。”
“臣虽然忙碌,但写一篇文章的时间还是有的。真师既如此看重,不如臣回去抽空写上一篇?”顾铮主动道。
贺卿惊讶地看了他一眼,点头答应,“顾大人若能写,自然最好,只是怕误了你的正事。”
“无妨。”顾铮闻言微微蹙眉,脸上的神色淡了许多,摆手道。
看他的神情,贺卿总觉得像是出了什么事,只是她的身份不方便询问,便只能压下这个念头,跟顾铮约定好了大致的字数和交稿时间,然后把人送走了。
顾铮的心情的确不怎么痛快。近来朝中许多蛛丝马迹,都显示着恐怕会有大事发生,而且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那种,因此他的心情十分恶劣。不愿意面对,就找了个借口出来,然后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就走到这里来了。
如今,闲暇时看看报纸,也是他唯一能放松的时候了。官场的尔虞我诈暂时远去,能与志同道合之人神-交一番,足可弥平许多烦恼。
但对他而言,这种休憩是短暂的,很快又必须要打起精神去面对。
这一期报纸发出的那天,宫中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小皇帝病了。
成长期的婴儿,发热是很正常的,而且温度并不很高,当是小病。但这病既然生在皇帝身上,就不可能是小事了。太皇太后震怒,伺候的人从奶娘到洒扫的仆妇,全都被处置了,就连张太后这个做母亲的,也被申斥了一番。
但这只是对外的说辞,实际上,在内部,事情并未止步于此。
也不知道太皇太后那边的人是怎么查的,反正一番弯弯绕绕之后,事情跟宫外的人扯上了关系,是最近才入京的几位藩王。
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几位藩王,俱是当日林太后乾光宫问计时,朝臣们举荐的储君人选。本该在几人之中择选一位,最后因为张太后意外查出身孕,这才不了了之。
但现在看来,太皇太后并未因此就放了心,而是打算斩尽杀绝,不给他们留下任何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知情者都不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
于是几位藩王的“罪状”,便被公布了出去。妄图谋害皇帝,这是谋逆造反,也是朝廷和皇室绝对容不下的罪名。此事一公布,朝中一片哗然,本来因为登基大典而充满喜悦的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
大多数人对此事还是怀有疑虑的。
且不说这些藩王才入京没多久,有没有这样的门路、手段和势力去做成这件事,便是有,也绝对不会是让小皇帝受一场寒这么简单。既然得了机会,要弄死一个婴儿再容易不过,为何还要留下隐患?
不是没有官员上疏,为这几位藩王辩解或是求情,然而在这件事情上,太皇太后可谓是铁石心肠。
一开始还只是申斥,后来见奏疏没完没了,索性就开始株连。下旨晓谕百官:凡上书求情者,一概视为谋逆同党!
这份诏书一发,上书的人立刻没了踪影。
毕竟证据确凿,而且涉事的只是藩王,并未牵扯到文臣,也不值得他们豁出性命去救。在政治上,宗室王族同样也是文臣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是能与他们争权的存在,必须要小心警惕。
没有了阻碍,事情倒是处理得很快。太皇太后以不要影响接下来的登基大典为由,将几人低调处理了。这份手段,该知道的人都已经知道了,该威慑的人也都威慑了,效果也非常好。
至少很多入京时还显得张扬的宗室,自此以后都夹紧了尾巴做人。
只是朝堂上,几位相公的情绪都不高,虽不至于愁眉不展,但任谁见了都知道心绪不佳。而已经上了无数次致仕奏疏,只因小皇帝尚未正式登基,所以一直没有被允许归老的薛知道,更是直接病了一场,连早朝都不上了,一应事务都推给了其他人。
因为几位相公都与此事有关,知道自己在太皇太后那里挂了名,因此都不愿意张扬,倒是让接手了不少事务的顾铮,在朝中地位越发显赫了。按理说,他应该是这一场政治斗争的得利者,虽然他从头到尾都未曾参与,但顾铮心里却并不高兴。
这是一场他早就预料到,却根本无力阻止的争斗。
它发生得毫无意义,只除了……让养寿宫那位太皇太后在朝堂上的权威变得更加沉重。
第32章 奢侈靡费
往常,帝王登基总是在大行皇帝孝期之中,因此虽然规仪隆重,但其实并不靡费,一应庆贺之仪皆被免去,如设宴这等事,更是从未有之。
但这一次却不同以往,先帝的孝期已经过了,又适逢太皇太后才刚刚在朝堂上立威,正需要加恩以安抚人心,自是不会吝啬举办各类庆典。
所以此番登基大典,不但从宫中到京城各处张灯结彩,绸缎装饰,更是舞乐频开,官民同乐。事后统计,光是这一场庆典之中便靡费近百万,令人触目惊心。
大楚比照前朝,于国库之外另设皇帝内库,名下有田庄店铺作坊等,专供皇室所用,足以承担整个皇室宗族的费用,甚至偶尔还会有所盈余,用于补贴国库所缺之额。
但那只是正常情况下。
在这之前的两位皇帝,灵帝和献帝都不是什么正经人,花起钱来更是没有半点数,数代积累的内库早就被他们消耗一空。非但不能补贴国库,还年年都要国库再拨一大笔钱进来。
毕竟,偌大个朝廷,总不能让皇帝没有钱用吧?
这两年天灾频仍,地里的出息自然也不好,国库能收上来的税,往往只有惠帝年间的七八成,用以维持朝廷各项开销,本来就已经很着紧,还要贴补内库,着实苦不堪言。
户部尚书这个位置,如今简直比政事堂的相公还难做。光是献帝在位这两年间就换了三任,目前仍旧空置着,只由两位侍郎处理日常事务。
原本太皇太后秉政之后,因她素行节俭,这一年多也并无任何奢靡之意,着实令朝臣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她懂不懂政事,能不能决断军国重事都不重要,只要能够保持住这种简朴风格,信任朝中重臣,说不得朝堂反倒会比之前二十年更清明,绝不至于耽误大事。
然而不过一年时间,太皇太后就变了一个人。
一次庆典花掉近百万,就连灵帝最荒唐的时候,也不曾如此。
虽然这其中最贵重的是各种绢帛物事,真正用掉的现钱只有十几万两,但这个数量已经足够令人震惊,而且这些钱,还都是从国库掏出来的。
因为之前太皇太后处置几位藩王立威,也因为此事,登基大典的整个安排过程中,政事堂的重臣们都显得忧心忡忡,等这最终的账算出来,就更是气氛凝滞、山雨欲来。
这其中花的最多的大头,一是做各种表面功夫,譬如在京城各地都装点上彩绸花灯,二是给百官和勋贵藩王的各种赏赐。
这么大的庆典,文武官员和各地都有贺仪送上,朝廷便要翻倍的赏回去。但人家献上来的都是各种祥瑞之物,除了说着好听看着好看,没有任何用处,赏下去的却都是金银钱帛。
一进一出之间,等于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若只是花钱,还不值得诸位重臣如此忧心。毕竟朝廷已经节俭惯了,他们也都已经适应这种一文钱掰开成两文来花的环境,没钱了设法节省便是,这么多年都是这般过来的。
真正让他们觉得忧虑的,是太皇太后这种花钱如流水的态度。
她自己的生活其实到现在为止仍旧不怎么奢侈,每天的菜品都要比照份例减去几个,一应用度并无出格之处。然而涉及到“脸面”这两个字,太皇太后花起钱来,却是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般好大喜功,爱做表面功夫,绝非朝廷社稷之福。
参政知事姚敏与顾铮关系一向亲近,这日散衙之后便来找他出去喝酒,席间不免苦闷地多喝了几杯,抱怨道,“前几日才得了奏报,甘夏数州又遭了蝗、旱之灾,今年怕是颗粒无收。只因登基大典之事,政事堂暂且将消息压下去了。这一场庆典,银子流水般的花出去,最后得了什么?若用来救灾,又能活多少人?”
“便是如此,倒也罢了,怕只怕开了这个口子,往后无穷无尽,终成祸患。”
“此事政事堂可有决议?”顾铮转着手中的杯子问。
“刘相公以为当组织官员上谏,阻一阻这种风气。汪参政却不同意,认为太皇太后如今正在兴头上,贸然上谏,绝无好处。”姚敏叹了一口气,“薛相公不在,刘相公压不住下头的人,只怕一时三刻难以决断。”
“汪参政的话倒也有些道理。”顾铮道,“太皇太后……对朝臣本就不甚信任,若是此时贸然上谏,恐怕只会惹恼她老人家,届时更难收场。”
“此事,顾兄可不能不管。”姚敏闻言抬起头看向他,半醉的表情中还能看出两分认真,“若能解决了此事,于你顾玉声而言,却也不是坏事。”
政事堂如今没有压得住事的人,人人都知道薛知道走后就是顾铮上来。既然如此,若他能解决了此事,声望自然更高,入主政事堂才算名正言顺。
顾铮微微一怔,而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含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