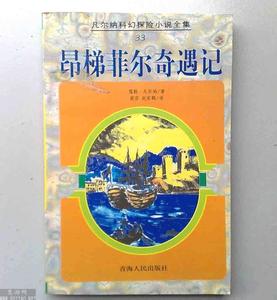平格尔的奇遇-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微笑着说:“我们马上就要吃好吃的东西了。”
我抬起头来看那只训练有素的猴子怎样做。可是使我奇怪的是,它并不想采集椰子,而是心平气和地坐在树冠上捉跳蚤,根本不理睬我们。
“它往往这样,”农舍主人抱歉似的说,然后对猴子大声喊道,“巴杜——巴杜——快点!”
然而猴子只是专心干它那称心如意的活儿。它敏捷地捉着跳蚤,用锐利的牙齿把跳蚤咬碎,然后朝我们啐来。
不管主人怎样喊,也不中用。
我决定恫吓一下巴杜,就从头上摘下帽子,朝空中抛去。
巴杜对这种举动发生了兴趣,龇着牙齿,好像在微笑。于是我又照样做了一遍。
巴杜看着、看着,忽然很快地站了起来,摘下一个大椰子,用力向空中抛去。
这颗炸弹掉下来的时候差点打碎我的头,不过我总算躲开了。这时主人也躲到农舍里去。
巴杜这才想起了它的差事,于是立刻带着另外一个椰子爬了下来,放在农舍的门前。
主人用钻子在椰子壳上钻了一个洞,把里面清凉甜美的白色液汁倒在碗里,递给我喝。后来他又把一个木头楔子钉进洞里,把椰子壳劈成两半。椰子中间的白瓤很好吃。我津津有味地吃完了这种热带食物。巴杜也得了一份,它带着那块椰子回到屋顶上去了。
我时常觉得奇怪,命运为什么对一些人那样慷慨,让他经历各式各样的事件,而对另一些人却那样吝啬,让他们始终过着平凡无聊的生活。不过,和我后来的遭遇比较起来,马戏团里的表演和密林中的旅行又实在不算一回事了。
在这次徒步旅行中,有时我在农民们的木房子里找个栖身之处。我学会了在地上睡觉,并且对于有块玉蜀黍的烤饼当晚餐感到满足。有时我还得睡在露天里。
有一次我迷了路,找不到人们指点给我的村庄。累得我筋疲力尽,倒在布满石头的小路上,躺在那里恐惧地想着这种孤立无援的惨况。我的葫芦水壶里,一共只剩下两口水了。
一只蓝色的大蚂蚁,转动着混浊而碧绿的眼睛,从干硬的土地上朝我爬来,想咬我的脸。我喘着气,举起拳头捶扁了这个昆虫。这件事使我想起:我是一个人。
天黑了。爬虫在蕨类植物①的下面机灵地穿来穿去,发出沙沙的声音。雪豹在山上的森林中嗷嗷地吼叫。
「①高等孢子植物的一个亚目。草本植物,有少数是木本植物。叶子有的非常分裂,有的十分复杂,形成叶状茎。主要产在热带和温带森林中。——译者」
我朝一旁爬去,爬到一条小溪旁边,喝了几口水,总算解了渴。后来,我就爬到树上去过夜,免得碰上野兽,发生意外。
睡过一觉以后,我的精神振作起来,虽然我的肚子和旅行袋同样地空,可是我还是鼓起余力上了路。
这条路把我带到了一个广阔的林中旷地,那里有一个由茅屋组成的村庄。我吹着足球队员进行曲的口哨,装出我是精神奕奕的样子走进了村庄。
我向村边的一家茅屋里面看了看。一个活像骷髅的印度老头坐在炉灶旁边,似乎得了热病,正在浑身发抖。他那肮脏的、瘦骨嶙峋的腿细得简直像两根棍子,胯股上盖着一条破旧的布巾。
我用乌尔都话向老人问好:“您全家平安,老大爷。”
老头回答了句什么话,接着就咳嗽起来。
“这个可怜的人大概得了肺炎。他怎么能顾得上我呢?”我想,于是走向另一个茅屋。
在那个茅屋里,一条破席上躺着几个人,也都在咳嗽。第三个茅屋里也是几个人在躺着或是坐着咳嗽。
当我把头探进这个茅屋的时候,一个妇人工把一碗水递给一个躺着的人,她见了我,惊慌地问道:“这个人要干什么?”
我走进茅屋,向那个妇人问道:“他们在哪儿受了寒?下冷雨的月份早过了,怎么这儿的人却害起肺炎来了。得做保温压布。”
我在学校里听过一些用压布治病的方法。现在我很可怜这些不幸的人,他们喘得这么难受,让痰堵得上气不接下气。要是我们那个弗利特大夫在这儿多好!他知道怎么制服这害人的喘病。
妇人蹲在那里,摇着头说:“唉,年轻的大人,一眼就能看出您是个善心人。那个老大夫连理都不理我们,早晨他从炮台来到我们这儿,一看见我的丈夫萨哈威特咳嗽,就连忙从屋里跳出去,蹦上马走了。您年纪轻轻的,倒有慈悲心。让菩萨保佑您长寿吧!”
喘得很痛苦的萨哈威特躺在席子上,吃力地朝我转过头来,嘶哑地说:“让菩萨保佑您出门人钱袋里的卢比越来越多吧。走吧,我们要死啦,别在这儿看着吧。”
在这个茅屋里,是休想休息一会和找点东西吃了。
在第四个茅屋里,我遇到的情形也一样,住在茅屋里的人——男人、女人、小孩子——都躺在那里咳嗽。
我想,这无疑是个结核病猖獗流行的村庄,与其呆在这些肺痨病人中间,不如再往前走,找个碉堡,也好讨个栖身之处。这次旅行把我弄得相当劳累,我已经打算回到种植园里工作。因为,办事员的地位毕竟还能带来点面包和一个住处啊。
于是我这个不走运的流浪汉就离开了村庄。太阳还很高,可能像人们告诉我的那样,在天黑以前走到碉堡,哪知离开村庄以后,还没走出一英里,就遇到两个穿着我们殖民地军队①制服的士兵,从矮树丛中走出来,举枪对我瞄准。
“回去!”
“这是怎么回事?”我举起双手央求道,“我投降就是了——”
“回去!”我所得到的却是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不然就开枪了。”
子弹飞过我头上的轻微啸声不容我再说什么话。我不择道路地往回跑。
一枝系着纸条的箭射到我的前面,平稳地落在布满尘土的枯草上。
我取下纸条,读了上面的铅笔字,结果把我吓得全身冰凉:“纳布哈特发生鼠疫。禁止越过插有黄旗的地带,否则格杀勿论。巡逻队长波洛。”
树林边,离我几百码②远的地方,站着另外几个巡逻兵,在那里挥着手,叫喊着什么。
「①作者写本书时,缅甸还处在英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所以这里称殖民地军队。1948年,缅甸独立为共和国。——译者」
「②码是英国所用的一种长度单位,一码等于3 英尺或0。9144米。——译者」
我刚往前迈了一步,就是两枪打了过来。我被这个意外情况弄得一筹莫展、在绝望之中,只得垂头丧气地往纳布哈特走回去。枪弹或是鼠疫,反正都得一死。可是孤零零一个人,实在可怕。我因为不放走进那些茅屋(那里面总是发出嘶哑的咳嗽声音),就在布满尘土的道路上坐下,闭上眼睛,就这样至少坐了一个小时,因为我讨厌看见这个丑恶的世界。我听见在远处打了几次枪,可是我连动也没有动。就让枪弹打中我吧——
后来我听到了什么人的脚步声。
“坐在路当中可非常不妙啊,”一个沉着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着,我睁开了眼睛。
有一个人戴着一顶白色的软木帽和二副太阳眼镜,穿着一件宽大的短衫,肩膀上挎着两个皮包。站在那里注意地看着我。
“难道我碍着你啦?”我用十分粗鲁的口气问他。
“村子里在闹鼠疫,我劝你不要吸进尘土,”那个人回答,他并不注意我问话的腔调,“起来吧,我们到比较僻静的地方去。”他微笑一下,“别固执,要听年纪大的人的话——”
这些话说得充满好意,所以我听从了——
我们来到一垛矮石墙的荫影下面。那个人用手帕擦了擦脸,说:“真糟,你想必是要到根奇去,可是迷了路,结果哨兵让你受了些惊吓。喂,提起点精神回答我。那些个蠢货开枪威胁过你,是吗?”
“是的。”
“嗯,没有办法。只好等死啦,等到小黄旗圈起的地区里的人都死光了的时候,那些兵就会把纳布哈特酒上煤油,放火烧光。”
远处砰砰地传来了射击的声音。
“这是哨兵在打死那些从鼠疫地区跑出来的狗。”
“那些人呢?”
“凡是生病的人都躺着;许多人已经死了。”
“以后怎么办呢?”我问道。
“以后就把地翻耕一遍,把洞穴里的黄鼠捉光,把一切东西都洒上漂白粉。再过一年,这块地方才能住人——”
我陷入了绝望中。一切都完了,我们被封锁了。鼠疫的魔鬼、比老虎和雪豹更可怕的细菌要把我们在这里折磨死。可是小黄旗的那边,却有枪弹在等着我们。谁也不能从这里活着出去,得了鼠疫是没有救的。
我皱着眉头看了看和我说话的人。他那刮得光光的、有一条条细皱纹的脸,镇静得令人惊讶,一双锐利的灰色眼睛正在注视着我。
“您大概是在研究我的相貌吧?”我极力装出笑脸,因为我不愿意让这个死亡的候补人看出我害怕鼠疫。
我听到他回答说:“您说对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到过贝尔港吧?”
我喃喃地说:“去过一次。”
那个人接着说:“请原谅我这样噜苏。请问您是不是有一次从跳台上跳下去救过一个溺水的人?”
贝尔港的事生动地重现在我的脑海中,于是我说:“谁处在我的地位都会那样做。我看见一个洗海水浴的人向海底沉下去,我就跳了下去。可是我始终没有看清楚我救起的那个人。”
那个人站了起来,和我握了握手说:“让我来谢谢您。这么说,是您救了我。当时人们把我从您的手里捞上救生船,马上送到城里去了。”
我和他握了握手,说:“看见您很健康,我很高兴。可惜我们在这种时候碰见——”
“我们不要尽想那些不痛快的事吧。我是个生物学家,所以自然界对于我并不像对于别人那样可怕和神秘。我叫密尔洛司,请多指教。”
“我叫平格尔,”我用迪仁学院的派头彬彬有礼地鞠着躬说。
“很好,平格尔,”密尔洛司好像在思索什么似的,接着他立刻说,“好吧,咱们先来吃点东西再说。”
密尔洛司从皮包里拿出一些面包干和罐头。
“要是有杯水,再加上几滴糖酒,那就太好了。”他边说边从旅行壶里往小杯子里倒着糖酒,“平格尔,你先喝了这个,然后再吃东西。”
他留心听着从茅屋里传来的咳嗽声。
“那是典型的肺鼠疫——这种病是由一种细菌引起的。它们是从寄生在啮齿动物,多半是老鼠、土拨鼠、跳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这里的人用套索捕捉这些啮齿动物。有一次,不知哪一个本地的猎人剥了感染了鼠疫的动物的皮,把它挂起来,就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密尔洛司的糖酒是烈性酒。喝了以后,我心里轻松了一些,于是试着开了句玩笑:“密尔洛司先生,看来您同鼠疫的关系搞得很好吧?”
这位生物学家沉思地看着自己的手指尖。
“在这一带有两种鼠疫,一种叫做‘瓦巴’,得了这种病的人,几乎都活不成,而且死得很快。另一种叫做‘马利’,发展得比较慢——平格尔,您为什么不吃?”
一块火腿面包卡在我的喉咙间咽不下去了。密尔洛司的话使我心惊胆战。我极力保持着镇静,因为我面前这个人谈到鼠疫时却是那么神态自若。
“平格尔,现在你仔细听着。我研究过很多年鼠疫,早就给自己接种过抗鼠疫疫苗,因此我不会感染鼠疫,我既能抵抗‘瓦巴’,又能抵抗‘马利’。以德报德,现在我要帮帮你的忙。可是我只带着预防‘瓦巴’的抗鼠疫疫苗。要是你还没有感染上‘瓦巴’,那么在接种以后它也许就不至于再给你添麻烦了。可是如果现在包围着我们的是‘马利’,”密尔洛司用探询的眼光看着我,“那么科学就没法帮你的忙了。”
我低声地说:“这么说,连预防‘瓦巴’也不顶有把握,是不是?密尔洛司先生,我倒很想活下去呢——”
密尔洛司说:“把胳臂伸给我,平格尔,转过脸去。不要看我怎样做。”
过了一分钟,我觉得他在我左前臂上打了一针。我听见这个生物学家问道:“怎么样,平格尔?”
“很舒服,”我含糊地说,同时感到一种奇异的刺激。
“不发冷发热吗?”
“不,不,”我低声说。可是我的牙齿在打颤,上下腭让不愉快的痉挛弄得抽搐起来。
密尔洛司抓住我的胳臂,摸了摸脉搏。
“打起精神来,平格尔。这种轻微的神经兴奋现象很快就会消失的。我来帮你挪动一下,好坐得舒服一些——”
我们坐到了树下一块石头上面。
密尔洛司说:“我去侦察一下。可是你得极力保持安静。”
他走了,我很高兴。因为这个唠唠叨叨的人惹得我很不痛快。
深红色的月亮升起来了。豺狼在远方的矮树丛后面悲惨地呼啸。在这旷地的那一头,靠近树林边,发出了士兵们吹哨和呼唤的声音,接着传来几声响亮的枪声。难道密尔洛司在小黄旗附近被他们打死了吗?他大概是想从这个死亡的发源地跑出去吧。
后来,在即将破晓的浅蓝色天空的背景上,出现了一个中国人,他俯着身体,用探索的眼光看着我。
过一会儿,那个中国人忽然不见了,而沃尔松先生却和蔼可亲地朝我微笑。
我睁开了眼睛,密尔洛司站在我的面前,问我:“平格尔,你不咳嗽吗?很好。要是想咳嗽,就脸朝下躺着。这样会好过一些。”
在阴暗的树林上面,月亮发着浅红的颜色。病人的咳嗽声和稀疏的枪声,不时打破这个热带之夜的沉寂。
密尔洛司留心地听了听,“他们已经把所有的狗都打死了,还打死了一个女人。现在开枪,是怕有什么疏漏。他们知道我,可是他们还是担心我们要从这里逃出去。当然,在我们这方面来说,跑出去是不太好的。为什么要把我们应该受的惩罚分给那些不相干的人呢!”
这话把我气坏了。
“我什么惩罚也不该受。您说的只是您自己。密尔洛司先生,您要知道,我本来是无论如何不愿意离开家乡的,可是我要生活啊——”
太阳升起来了。我口渴得非常难受。我的壶里的水早已喝光了。茅屋里的水会传染鼠疫,而干净的井水又在小黄旗的那边。
密尔洛司说:“你要是把灰尘咽下去就坏了。你得慢慢呼吸,而且只能用鼻子呼吸。这可以预防——”
他给我在鼻子和嘴上戴了纱布口罩。我是无所谓的,所以就随他把口罩的带子系在我后脑勺上。
石头让太阳晒得滚烫。我们坐在歪斜的矮墙下,用鼻孔小心地吸着难闻的空气,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很走运,总算没有风。一些长着长须、形状像蛾的小虫在矮墙上爬来爬去。行动灵活的蜥蜴一动不动地贴在发烫的石头上,无忧无虑地眨巴着小眼睛,在阳光照耀下,它们是多么幸福啊。鼠疫并不伤害自然界中的这种小生物。
密尔洛司说:“我们要防止身体衰竭。”
我似乎迷迷糊糊地看见,他用手敏捷地按住了一个蜥蜴,捉住它,把它吃了。吃了点东西以后,他的话更多了:“纳布哈特一共有十九个茅屋,大概有十一个茅屋里的人都死光了。”
这一天长得好像老是过不完。沉寂,像命运一般残酷无情的沉寂,慢慢地、凛然地降临到这个可诅咒的、孤零零的村子里。茅屋里的咳嗽逐渐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