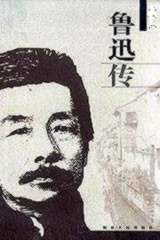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与寿洙邻的谈话,录自寿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
事》,文收绍兴鲁迅纪念馆1986年编印《乡友忆鲁迅》。
(周粟说,在北平能买到鲁迅的书,只是都是翻版,印的不好,错字也多)
“这是没有办法的——不过翻印也好,大家能够看到就好,在这里简直就不准卖。”
·与周粟的谈话,录自周粟《鲁迅印象记》,
文刊1936年11月1、2日《西京日报》。
“我的生活一天就是在屋子里坐着,不能外面去,找不到新材料,所以不能作。”
“翻译一点东西,还出一本《二心集》。”
·1932年11月25日与王志之、张松如、潘炳皋的谈话,录自
潘炳皋《鲁迅先生访问记》,文刊1932年第4期《北国月刊》。
上海报刊上确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论调,(指鲁迅文章写得好,完全是由于鲁迅精通古文的缘故。鲁迅反对这种论调,但事实上这种论调有其正确的一面/编者),这是古董家骗人的话。其实,我的初期作品多少夹杂着一些古怪的字眼,但这不是金子,而是沙砾!我的白话好像小脚放大脚,所以这种白话是不纯洁的,不健康的!所以纯洁的,健康的白话,只有在年青的一代,没有受过古董的毒的年青的一代才能产生!
·与俞荻等人的谈话,录自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
厦门大学》,文刊1956年10月号《文艺月报》。
“这种书还在这样地出售(指鲁迅作品被一再重印/编者),说明没有代之而出的新书。这样看来,这个社会还没有进步。”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景宋《鲁迅先生
的精神》,文刊《上海鲁迅研究》第6集。
我打算在生存的时候把自己的全集编起,大约以二百五十万字为标准,要是可能,今年(指1932年/编者)就希望编成的。
·与孔另境的谈话,录自孔另境《我的记忆》,文收
孔另境著,泰山出版社1937年6月版《秋窗集》。
我自从一九○六年二十六岁中止学医而在东京从事文艺起,迄今刚刚三十年。只是著述方面,已有二百五十余万言,拟将截至最近的辑成十大本,作一纪念,名曰《三十年集》。
您所在的位置: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正文回目录
第30节:与冯雪峰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文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比较起来,我还是关于农民,知道得多一点。
要写,我也只能写农民,我回绍兴去。
其实,现在回绍兴去,同农民接近也不容易了,他们要以不同的眼光看我,将我看成他们之外的一种人,这样,就不是什么真情都肯吐露的。
……
现在的产业工人里,我没有一个朋友。我不熟悉他们的生活,不熟悉他们的脾气。单以街头上看见的去写,是不行的。像外国的作家,根据材料和调查去写,也许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能用的办法,我们还是不行的。写报告文学可以如此做,要创作我总以为不好办。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我总想把绍兴社会黑暗的一角写出来,可惜不能像吴氏(指吴敬梓/编者)那样写五河县风俗一般的深刻。
不能写整个的,我就捡一点来写。
·与张宗祥的谈话,录自张宗祥《我所知道的鲁迅》,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我的小说都是些阴暗的东西。我曾一时倾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等人,今后我的小说也将都是些阴暗的东西,在中国能够有什么光明的东西吗?
·与山上正义的谈话,录自山上正义作李芒译《谈鲁迅》,
文刊1928年3月号《新潮》,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
偶然有一点想头时,便先零碎的记下来,遇到或想到可写的人物特性时,也是如此。这样零碎的记录在心里慢慢融化,觉得人物有了生命,这才将段片的拼凑成整篇的东西。全篇写就以后,才细看哪些地方要增删。最后注意到字句自然的韵调,有读起来觉得不合适的字眼,再加以更换。
我的文章里找不出两样东西,一是恋爱,一是自然。在要用一点自然的时候,我不喜欢大段的描写,总是拖出月亮来用一用罢了。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张新颖编,
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鲁迅印象》。
“我的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不是老大就是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能提一句,以免别人误会。”
·与客人的谈话,录自许广平《所谓兄弟》,文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
“他们(指列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编者)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得烈夫(现通译“安特莱夫/编者)有些影响。”
·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武定河(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
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文
刊1937年3月25日上海《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
(姚克说,鲁迅的小说“还保留着旧小说的风格”)“我想你所说的是对的。以前我看过不少旧小说,所受的影响很深。但我却并不是有意模仿那种风格。我喜欢新的技巧,不过现在还只在学习。”
·与姚克的谈话,录自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悼念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5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你可注意到过散文的声调?我自己写完文章后总要细读一两遍,字的声调有不妥当的改一改。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可以让别人去完成这个不朽的大业(指《中国文学史》/编者)罢,我还是去写点教授学者所不齿的杂文。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此种文章(指为论战而写的杂文/编者)发表出去,凡可能反响,我都一概计划在内,对方怎么来,我怎么应付,都想得周周到到。
·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
一个名字声音和你的相似,而姓不同的人所写的旧体诗词,是否是你用化名写了开开玩笑的?
积习难改,偶然写一首,但不发表,因为怕影响文学改革。偶然有点感触,不敢高攀天才所膜拜的“灵感”,旧体诗对自己仿佛比新体诗便当一点。
·与李霁野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
一天,母亲问我说:“人家都说你的《呐喊》做的好,你拿来给我看看如何?”及看毕,说:“我看也没有什么好!”
·与章衣萍的谈话,录自章衣萍著,北新书局1929年6月版《枕上随笔》。
“捷克人来翻译我的东西,我倒高兴,已经签名做序。”(指收于《鲁迅全集》第6卷中《〈呐喊〉捷克译本序言》/编者)。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同鲁迅先生最
后的晤谈》,文刊1936年11月20日上海《逸经》
半月刊第18期,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
“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我虽然悲观,但到今日的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代,也许不至于“吃人”了,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我一听见《呐喊》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他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
您所在的位置: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正文回目录
第31节:与孙伏园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呐喊》的畅销,是中国人素来拒绝外来思想,不爱读译作的恶劣根性的表现。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曾秋士(孙伏园)《关于鲁
迅先生》,文刊1924年1月12日《晨报副刊》。
由于钱玄同先生的劝勉,才开始写《狂人日记》。
·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景宋《藏书一瞥》,
文刊1947年1月9日上海《文汇报》,转自
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鲁迅》。
我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了外国文。
(孙伏园问《孔乙己》的好处)
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的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曾秋士(孙伏园)《关于鲁
迅先生》,文刊1924年1月12日《晨报副刊》。
(孙伏园一次问先生,在他作的小说中他最喜欢哪一篇)
“是《孔乙己》。”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著,1942
年4月作家 版《鲁迅先生二三事》。
(孔乙己)也实有其人,此人姓孟,常在咸亨酒店喝酒,人们都叫他“孟夫子”。
(我)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著,作家
1942年4月版《鲁迅先生二三事》。
《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谈〈药〉
——纪念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0日
(北平)《民间》半月刊第3卷第13期。
在西洋文艺中,也有和《药》相类的作品。例如俄国作家安特莱夫,有一篇《齿痛》(原名BenTobit)描写耶稣在各各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各各他附近有一个商人患着齿痛,他也和老栓和小栓们一样,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个革命者的冤死来,重要得多。
……
还有俄国的屠尔介涅夫(即屠格涅夫/编者)五十首散文诗中有一首《工人和白手的人》,用意也是仿佛的。白手的人是一个为工人的利益而奋斗至于牺牲的人。他的手因为带了多时的刑具,没有血色了,所以成了白手。他是往刑场去被绞死的。可是俄国乡间有种迷信,以为绞死人的绳子可以治病,正如绍兴有一种迷信,以为人血馒头可以治肺痨一样,所以有的工人跟着白手的人到刑场去,想得到一截绳子来治病。不知不觉中,革命者为了群众的幸福而牺牲,而愚昧的群众却享用这牺牲者。
·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谈〈药〉
——纪念鲁迅先生》,文刊1936年11月10日
(北平)《民间》半月刊第3卷第13期。
我是真的遇见了那件事,当时没想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洋车夫,竟有那样崇高的品德,他确实使我受了深刻的教育,才写那篇东西的(指《一件小事》/编者)。
·与孙席珍的谈话,录自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文收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
“这‘猹’字是我自己造的。”
“不是,比‘刺猬’还大。”
“是乡下人说的,我也不大了然。大概是‘獾’一类的东西罢?”
·与章衣萍的谈话,录自1930年5月5日章衣萍
致柏烈威信,文收1988年第11期《鲁迅研究动
态》中强英良《一位苏联人和一部苏联小说集》。
“只是由于《北京晨报》编者的缘故,使小说有这么长的的篇幅。第一章登在《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内,编者认为它只不过是反对孔教信徒的讽刺小品而已,第二章才看出是某种小说,就把它移在‘新文艺’栏内发表。我本来是一开始就想把阿Q杀头的,但是,一连几个星期,编者一直不许我结束这部小说,我就继续往下写。最后,趁编者休假离任,我才把阿Q的灾难结束了。”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著佩云译
《鲁迅——白话大师》,文刊1935年1月美国
《亚洲》杂志,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
我写《阿Q正传》,原是想通过阿Q的形象,指出各种各样的坏习惯和坏脾气来。
·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呐喊分析》,文收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说不尽的阿Q》。
(斯诺问:“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
“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
·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录自斯诺《走向abada…txt的旅行》,文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说不尽的阿Q》。
“阿Q比这(指商务印书馆出版,梁社乾译《阿Q正传》的封面,此封面为一德人所画,画中之阿Q,小辫赤足,坐在那里吃旱烟/编者)还要狡猾些,没有这样老实。”
·与章衣萍的谈话,录自章衣萍《窗下随笔》,文收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窗下·枕上·风中随笔》。
我是拿三个人结合起来成阿Q一个人的(指新台门中的外姓谢阿桂与其弟谢阿有,还有一个叫阿董的人/编者),当然重要成分是一个姓吴的。
您所在的位置: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正文回目录
第32节:与张宗祥的谈话
作者: 吴作桥
·与张宗祥的谈话,录自张宗祥《我所知道的鲁迅》,文载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
“看见的。”(指《中华日报》《戏》周刊上发表的袁梅的剧本《阿Q正传》/编者)
“我觉得很有趣。”(指袁梅剧本中让孔乙己、老拱、闰土等在《阿Q正传》剧本中出现/编者)
“只是那些话算是绍兴话吗?绍兴话那有那么多的‘者’?”
“那还是让我自己来翻译吧。不过全用绍兴话演起来人家怎么会懂?恐怕在上海一带演,要改成普通话吧?”
“那一恋爱场面可以写得很有趣。”
“不过我们绍兴乡下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酒店。招牌上也不写‘太白遗风’那样文雅的句子,顶多是‘不二价’。劈头看见丰子恺的画——一个工人靠在柜台上喝酒,旁边也写着‘太白遣风’,莫非外省酒店多有这样的句子么?”
“唔,有12张很不坏,不过他们画的阿Q都和我所想象的不同。我想象的阿Q还要少壮一点。还有是辫子问题。年轻的画家们‘去古已远’,对于辫子一道似乎不甚有研究,有的画家们把阿Q的辫子画得太下了,还得上去一点,因为从前农民的辫子是四周围都剃得光光的,只剩下一片脑上一个蒂的,有工作时往顶上一挽,很是干脆。”
“很好。不过得‘阿Q的地’说出来,我说‘阿Q的地’是说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