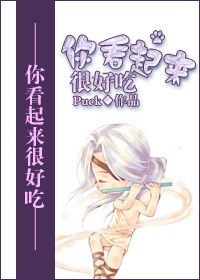你看我时很远 作者:西歌子(晋江2013-08-27完结)-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吗……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那老人把眉一扬,笑得比他更为舒畅,“哈哈,你就别瞒了,你这小子我还不清楚?你敢说你不想听那个故事的结局?”
“想与见你是两码事。”
“你会来找我的。”江曲回头看着那孑然的背影,步伐矫健。鹤发童颜,这是个形容他很贴切的词。他的自信究竟从何而来,江曲不得而知,江曲只是折服于他惊人的判断力,快,且准。
“喂喂,糟老头,你等等我,等等我啊!”江曲没底气地说着。阒静的海滩,昏黑的苍穹,海浪汹涌澎湃,白色的浪花不断冲击着他那酸胀的小腿。他听不到任何回答,只有一个低微诡异的声音在他耳畔厮磨,“你会来找我的,你会来找我的……”
他第一次见到苏英是在十七岁,那时候,他的父亲是工程师,他总是无奈地跟着父亲不分东西南北地跑。而那时候苏英连做梦都拿着数码相机,他觉得不用胶卷形成像是一件很神奇的事。苏英看见江曲还拿着胶片机到处拍照的时候,他甚至笑掉了一颗牙,真的,他笑得太入神,手舞足蹈的同时,他的佳能砸掉了他的一颗牙。
江曲看见那种带着腥味的液体从他嘴里蔓延出来,长白的虬髯宛若被顽皮的幼童泼洒了殷红的颜料,过街老鼠一般狼狈。
“哈哈,这是你侮辱胶片机的下场!活该活该!”江曲嘴上磨着刀,两只不听话的手却忙拉着他跑到海边,卷起衣袖,一丝不苟地为他清理血迹。咸咸的海水渗入伤口,他疼得直嚷嚷。
如果说苏英是老顽童,倒不如说他是只猴子,顽固不堪的臭猴子。
他捂着嘴,微疼的表情却还嬉笑,“本来就是嘛,你这小子落伍啦。现在随便走到哪条大街,他们手上拿的不是数码相机是什么!”
“哼,流行就一定好么?你不觉得自己在暗室里看着胶卷一点一点成型很妙么?”江曲瞋视着他,对主流的不满展现的淋漓尽致。他打了个冷颤,赶紧缩了缩身子,“唉,我老了,我不想循规蹈矩地活在过去,拿着回忆里辉煌过的东西高声欢唱,我要趁着我还活着多适应适应现在,你知道吗,一个人老去很孤独的。”
江曲没有应答,他默默从《旅游指南》里抽出他朝思暮念的那张脸,坐在苏英身旁陪他黯然神伤。过去是个死角,没有人进得去,躲在死角里的人拐弯抹角也寻不到出口。
苏英直勾勾盯住一脸愁容的江曲,心想,“小伙子情窦初开,想爱又不能爱的悲痛我也曾尝过。年少方不知世啊。”他一把抢过那张照片,本想让那少年走出情爱框成的牢,却发现自己似乎回到了那个青涩的年纪。“咦,婉眉?不……不是她,她眉心应该有颗朱砂痣,而不是这般逼人的英气……不是她,不是她。”
“婉眉是谁?”
“她是谁?”
然后,苏英开始絮絮叨叨地说他的旧情史。缺了牙的他,发音不标准,却让那少年听得神魂迷乱。
苏英是乡里唯一去城里读过书的青年,毕业之后,他选择了回乡教书。没过几年,中国开始闹文革,知识青年们都要接受上山下乡的再教育。婉眉就是下乡的女知青之一。
城里人都是没吃过苦的,跟婉眉一起下乡的女知青陆续都走了,有些是靠关系回了城,有些则是自残,捧着一摞病历单,才换了一张回城的通行票。可是婉眉却依旧干着农活,乐此不疲。
有一次,苏英带着孩子们出来写生,他瞧见那清河水波荡漾,红莲含苞欲放,美不胜娇。他也瞧见了婉眉坐在河边,她乌黑的头发梳成两根俏皮的麻花辫,漫不经心地抚着芦苇,印在水波里的那双灵动的大眼睛却默默地流着泪。苏英那时不知道,婉眉时常孑孓坐在清河边,拿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子,把自己的刘海剪得厚厚的,尽量让他们看不见自己的双眼,那因日夜反复流泪而又肿又红的眼睛。
他允诺孩子们去那边的小树林,但不可以走散,也不可以走远,过会儿就来找他们。他在婉眉身边坐下,拍拍她的肩,“是不是农村条件太艰苦了?如果觉得苦,也和她们一样回城去吧。”婉眉低眸颦眉,看着苏英那怜惜的目光,不禁绯红了脸。苏英看着她娇羞的模样,只觉得风吹清水芙蓉与碧叶红莲的温柔也抵不上拂过她的面容来得温柔。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静静地陪着婉眉坐着。他说,无言的陪伴比之无趣的闲谈有成效的多,至少,他让她的脆弱完全蜕摊在他面前,小心翼翼地让他呵护。
落日不知什么时候躲到了大山底下,孩子们纷纷捧着自己满意的画作来找他,他站起身,翻看着孩子们这一下午的成果,笑着夸奖孩子们有艺术天赋。婉眉也微笑着看着这群嚣闹的孩子,她说,感谢艺术被朴实的心赐予了灵魂。孩子们毕竟是孩子,才学疏浅,一股劲地晃脑,表示自己听不明白。苏英意味深长地笑着,嘱咐孩子们快点回家,不然父母该担心了。孩子们一哄而散,暗地里讨论着这位美丽的大姐姐。
他们就这样对上了眼,一有空,就跑到清河等对方。很多时候都是失望而归,可一旦两个人相见,就能开心上好几天。眼里的炙热散不去,心里的等待不会扑空。
可是后来,文革闹完了,婉眉也回城了。苏英孑然一人站在清河边上,无论怎么折芦苇,他也看不见那张朝思暮念的容颜了。他坐在清河边上,日复一日地看着日渐枯萎的莲。李璟有首词写得好:“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栏干。”温热的风随时光吹向远方,最终只剩苏英一个人乘一叶孤舟,穿梭在枯萎的莲叶间。
“苏英,你这身板还走这么快。”江曲放下他的胶片机,饶有趣味地看着苏英,“哈哈,你这臭猴子,往后的日子是不是不打算进食了?”苏英的牙不知道怎么又磕掉一颗,血液流淌,就像他们第一次见面。
“来找我了?”苏英忙着擦拭他的脸。
“恩,我来了。”
“我上次讲到哪了?”
“恩,婉眉回城了。”
“后来啊,我去城里看她,可是婉眉的母亲嫌我是个穷小子,说我不能给她幸福。那时候年少气刚,我说,两年之后,如若我没成就,我不会再见婉眉一面。如若我有出息了,婉眉就得许配给我。可是青春是不待人的,婉眉的母亲说,两年之后,即使我有了出息,婉眉的脸也要开始走向衰老了,她给了我两个月的期限,说是我筹到聘礼就把婉眉嫁给我。那时我又兴奋又气恼,兴奋的是她没刁难我,气恼的是她以为我看中的是婉眉的容貌。一个多月之后,我筹到了一半的资金,我写信给婉眉,叫她等我,等我带着她回清河。两个月还差三天,我筹够了聘礼的资金,我火急火燎地坐着火车去城里,可是那天,我们那几节车厢里有人抢劫,不论男女老少,我们都被带到了警署。我急着要走,却让他们怀疑,问了我好久的话。等我从警署出来,我穿着解放鞋一路跑到城里。可是期限过了,我眼睁睁看着婉眉撕心裂肺地哭着嗓子叫我骗子。然后没过几天,她被别人盖上了红盖头,走进了别人的红轿子里。”
“你们就没再见过?”
“再也没有。那年,我们确定关系的时候,婉眉讲过一个童话故事给我听,她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忍着伤痛行走的美人鱼,我们甘心等着日出将我们揉成泡沫,因为爱过,所以遗憾。”江曲不知道,苏英自己也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用尽了半生回忆。
☆、与莲花相依
苍茫天穹如同手中的玩物切实可即,厚重的云层与模糊的山峦相连,风卷残云,茕茕身影在浩瀚天地间不过如尘埃般渺小。顾离背上背包离开,眼里的惆怅似绵雨从天际汩汩流落,扬起的发梢飘来落寞的腐烂味。在失落面前,我们都是透明的冰块,等待恶魔举着火把将我们粉身碎骨。
程然拿出手机,按下一长串她并不熟稔的号码。依然是干净的铃声,可爱的音符在耳畔跃动。莲花在微风中婷婷而立,红艳似血,白嫩如雪。多少年前,少年在岸边伸手折下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轻摆在她耳畔,少年说——我的生命将与莲花一同盛开。她未理会少年,只是倾羡于渔舟唱晚。
“等志愿填好,我想去拉萨。你能……”
“我陪你去,好不好?”
“谢谢你。”
程然决绝地结束通话。她怕说太多会难过。她知道有个少年一直在为她默默守候,不论她是否在意,他都会聪明地隔着一段距离陪同她,装作顺路,偶尔开心地与她畅谈,以为自己把自己的心意掩盖地不露痕迹。
紫陌红尘,这纷扰的世间最美好之事莫过于有人在等。等待本就是极富浪漫却满怀悲伤的词汇,宛若樱花的残忍。没有人不害怕那个一直为自己守候的人在某一天突然回头,决绝地离开,不动声色。程然也不例外。她害怕白赟某一天遇见了比她更适合的人选,然后不顾一切地抛下自己,马不停蹄地奔向他方,将之曾经的热血、悸动、归属感与爱,加倍地给予另一个笑眸倩兮的美好女子。
注定等不到的人,何必再等?曾经握在手中的时光与感动,只需一声告别就完全流失。指尖的缝隙不会因为任何而消失。年少曾有过的疯狂,在某一刻必须被禁锢。为爱傻了那么久,荒废了似锦青春,却不见那人回头。那样的等待不值得。
好在程然回头的时候,白赟还在其身后,按捺着自己的欣喜,等着程然邀请他一同前行。他等到了!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春暖花开的生机勃勃也不过是他此刻心中一半的葱郁。他欣喜若狂,心里琢磨着:不论她是出于爱或感动,抑或只是偶然的孤独,我都会陪她一直走下去,哪怕有一天她亲手把我推下悬崖,我也要在半空中微笑着向她致别,虔诚地双手合十,向佛祖祈祷,让佛祖将我今世下世下下世的好运全都交付于她,只要她得以幸福——我只卑微地期望她会记得我,不论她是否知晓我爱她。这份爱由一颗卑劣的胚芽发育而成,自私亦无偿,卑微亦伟大。等至她回头,我之幸也。我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她与他人携手共进,亦是我之幸。
当然,他没有把这话告诉程然。他仍惶恐着,如果有一天她真的真的又要一个人走,或者选择与他人同行这残忍的做法,他终究手无缚鸡之力,他无法狠下心逃离有她的世界,哪怕一分一秒。几乎病态的想法。
程然和白赟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他们的志愿填的一模一样,默契也好,巧合也罢,他们都会在北方会和。程然说,看惯了碧水红莲,青石板街,深巷弄堂,百花争艳这等柔美百媚的诗意江南,对于北方的悬崖格桑,荒漠戈壁,劲松苍柏,草原广袤那般的奔放万里的狂野塞北是那样的着迷,灵魂都快被吸走。北方以北,放逐着她的梦。
白赟没有说话,他微笑地吻着程然扑朔的眼,灼热的温度,程然在恍惚中看见了幸福散出的耀眼光芒。那干净如水的光,在她心中波涛汹涌。白赟的孤注一掷,在她身上压上了一切筹码:幸福、青春、七情及其它不易解释的温柔,无论输赢,他都无法再脱身。他至始至终将自己比作她匆匆人生中最卑微的角色。可他何尝想过,她亦如此。
她亦不在乎自己前路如何,她只期许身旁的少年看她将一头乌丝染成白髻,陪她从豆蔻年华走进苍暮岁月,等到她面庞褶皱松塌,他仍用温润的手摩挲着她灼热的泪。前世的牵引,今世的相遇,下世的永恒。他们惺惺相惜,四目秋波起,与尘世背离,与莲花相依。
☆、世界侧脸的观望者
那是一个被遗弃的茶园,我叫它镜园。不大,周身的老旧铁栅栏由于年份久了脱了漆,一块一块的锈迹毫不忌讳地不断生长着。
这是我每次去镜塘必须去的地方。没有冰冷的水泥钢筋阻碍视线,也不会有各色的喧嚣来剥夺你可以安静的终身权利。很安静地靠着一棵茶树坐着。朝霞映天,冉冉斜阳,月落乌啼,静静地感受着时光一寸一寸地流逝,笨拙的手指,触摸着大自然的冷暖。
“沈若冰,快坐下。”
“这枝桠这么扎人,怎么坐啊?”
“你不是经常择物吗,物也会择人好吧。”
“好,你个大头鬼。”
自认为五官里长的最美的小耳朵经常做美梦,和青春期的女孩儿一样,无厘头地神游着,丝毫不计后果。幸而不解风情的枝桠还是会扎我,硬生生地刺痛我的肉体,刺醒我的灵魂。是,我该醒了。半途而废的人所受的痛苦都是咎由自取,临阵脱逃的人该受惩罚也总是理所当然。
记不得这是第几次来镜塘了。
那家家庭旅馆已经不在。随便选了一家小旅馆住下。
原来任何东西,终究会败给时间。只是,因为心里的时间的时差问题。
说来实在可笑,在镜塘一共待了六天,却是有四天实在旅馆里睡觉的。耳机很久没换,导致有些嘈杂,听不清歌词,只大概知道个调,倒也听得舒服。有些歌词写得太深刻,听得清楚反而是件坏事。
旅馆的每个房间都挂着一个钟,很复古的那种,金属制,钟摆晃来晃去的,有时候无聊盯着它倒是会安心很多。每个房间也都有阳台,是用很常见的花瓶栏杆包裹起来的,好好的花岗岩被喷上了土色的油漆,很别扭。别的和其它旅馆别无所异。
毕竟是小旅馆,人不多,老板娘都能认出谁是那个房间的住客,很贴心的感觉。
我问老板娘为什么要在房间挂钟,她莞尔,只是习惯看着时间流失罢了,总觉得很多事情没做或是做错了,它会提醒我去补做。
我却是一板正经,既然都过去了还怎么有机会补过,不可能了吧。
她摇摇头,笑的更厉害了,既然有心怎么会怕不可能,没试过又怎么知道不可能?
有心怎么会怕不可能,没试过怎么知道不可能。
原来只是一直在害怕。以为错过就永远错过,再补救也是徒劳。
那些错误,似水,一奔就不知何处是尽头。我拼命奔跑,紧跟着它们的脚步,可它们在某个地点分成了若干支流,以那样快的速度各奔东西,徒留我站在原地悲天。
六天很快就过去了。收拾行李只花了我五分钟,带的东西实在太少,明明是趟远行。
离开的时候老板娘叫住我,递给我一个信封,说,回家再打开,这是旅馆附赠的精美小礼物。她的笑容还是很甜,宛若一缕春风,一片狼藉的心里仅剩的生机都被唤起来,迫使人用最美的姿态还她一个最美的笑容,毫无平日的应付之意。
火车与铁轨摩擦发出的哐啷哐啷声还是伴随了我一路。回家没有直达车,转车是件麻烦事。背包很空,信被夹紧书里,书页上当然是常见的宋体,而白信封上是优雅的行楷,多看了几眼竟然觉得两种字体有些相类似了,毕竟都是一板一眼的白纸黑字。18小时的旅程,绵绵无期,由睡意引发的一连串幻觉已由不得人再倔着性子硬撑下去。
这一觉睡得很浅。依稀听得到列车员匆忙的脚步声,乘客因不满而摔杯子的碎裂声,还有不知是谁的梦呓。但是还是睡了很久,四小时,或许更久。
到童画的时候天已大亮。天空褪去浓重的黑色,只留下星星点点的白与蓝,错杂地融合在一起,不